和陳殿丞芍藥
化工余巧惜春殘,更發濃芳繼牡丹。
檀點藏心殷勝纈,異香迎鼻酷如蘭。
瓊樓窈窕仙家宅,云葉低垂醉里冠。
自有殊功存藥錄,不當獨取鄭詩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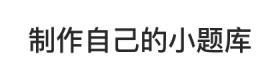
化工余巧惜春殘,更發濃芳繼牡丹。
檀點藏心殷勝纈,異香迎鼻酷如蘭。
瓊樓窈窕仙家宅,云葉低垂醉里冠。
自有殊功存藥錄,不當獨取鄭詩看。
大自然用盡剩余的巧妙心思,憐惜春天將殘,又讓芍藥綻放濃郁芬芳,接續牡丹。芍藥花心的檀點殷紅勝過彩纈,奇異的香氣撲鼻,酷烈如蘭。它如同瓊樓中窈窕的仙家住宅,花的葉子低垂好似醉者的帽子。芍藥在藥錄里本就有特殊功效,不應只從鄭詩里去看待它。
化工:指大自然。
檀點:指芍藥花心的顏色如檀木般。殷:紅。纈:有花紋的絲織品。
酷:極。
瓊樓:華麗的樓閣。
殊功:特殊的功效。藥錄:記載藥物的書籍。
鄭詩:可能指與芍藥相關的鄭國詩歌。
具體創作時間和地點不詳。當時可能正值芍藥盛開,詩人看到芍藥接續牡丹開放,被其美麗和香氣吸引,又聯想到芍藥的藥用價值,從而創作此詩。
這首詩主旨是贊美芍藥,突出其美麗的姿態、濃郁的香氣和藥用價值。在文學史上雖影響不大,但展現了詩人對自然花卉細致的觀察和獨特的審美。
鄰曲子嚴伯昌,嘗以《黑漆弩》侑酒。省郎仲先謂余曰:“詞雖佳,曲名似未雅。若就以‘江南煙雨’目之何如?”予曰:“昔東坡作《念奴》曲,后人愛之,易其名為《酹江月》,其誰曰不然?”仲先因請余效顰。遂追賦《游金山寺》一闋,倚其聲而歌之。昔漢儒家畜聲伎,唐人例有音學。而今之樂府,用力多而難為工,縱使有成,未免筆墨勸淫為俠耳。渠輩年少氣銳,淵源正學,不致費日力于此也。其詞曰:
蒼波萬頃孤岑矗,是一片水面上天竺。金鰲頭滿咽三杯,吸盡江山濃綠。蛟龍慮恐下燃犀,風起浪翻如屋。任夕陽歸棹縱橫,待償我平生不足。
百川異趨,必會于海,然后九洲無浸淫之患;萬國殊途,必通諸夏,然后八荒無壅滯之憂,會通之義大矣哉!
自書契以來,立言者雖多,惟仲尼以天縱之圣,故總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而會于一手,然后能同天下之文,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,然后能極古今之變。是以其道光明,百世之上,百世之下不能及。
仲尼既沒,百家諸子興焉,各效《論語》以空言著書(《論語》門徒集仲尼語),至于歷代實跡,無所紀系;迨漢建元、元封之后,司馬氏父子出焉。司馬氏世司典籍,工于制作,故能上稽仲尼之意,會《詩》《書》《左傳》《國語》《世本》《戰國策》《楚漢春秋》之言,通黃帝、堯、舜至于秦、漢之世,勒為一書,分為五體:“本紀”紀年,“世家”傳代,“表”以正歷,“書”以類事,“傳”以著人,使百代而下,史官不能易其法,學者不能舍其書。《六經》之后,惟有此作。故謂周公五百歲有孔子,孔子五百歲在斯!是其所以自待者不淺。
然大著述者,必深于博雅,而盡見天下之書,然后無遺恨。當遷之時,挾書之律初除,得書之路未廣,亙三千年之史籍,而局蹐于七、八種書,所可為遷恨者,博不足也。凡著書者,雖采前人之書,必自成一家言。左氏,楚人也,所見多矣,而其書盡楚人之辭;公羊,齊人也,所見聞多矣,而其書皆齊人之語。今遷書全用舊文,間以俚語,良由采摭未備,筆削不遑,故曰:“予不敢墜先人之言,乃述故事,整齊其傳,非所謂作也”。劉知已亦譏其多聚舊記,時插雜言。所可為遷恨者,雅不足也。大抵開基之人不免草創,全屬繼志之士為之彌縫。晉之《乘》、楚之《梼杌》,魯之《春秋》,其實一也。《乘》、《梼杌》無善后之人,故其書不行。《春秋》得仲尼推挽于前,左氏推之于后,故其書與日月并傳。不然,則一卷書目,安能行于世!
自《春秋》之后,惟《史記》擅制作之規模。不幸班固非其人,遂失會通之旨,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。班固者,浮華之土也,全無學術,專事剽竊。肅宗問以制禮作樂之事,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。儻臣鄰皆如此,則顧問何取焉?及諸儒各有所陳,固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,以塞白而已。肅宗知其淺陋,故語竇憲曰:“公爰班固而忽崔骃,此葉公之好龍也。”固于當時,已有定價;如此人材,將何著述!《史記》一書,功在十《表》,猶衣裳之有冠冕,木水之有本原,班固不通,旁行邪上,以古今人物強立差等,且謂漢紹堯運,自當繼堯,非遷作《史記》廁于秦、項,此則無稽之談也。由其斷漢為書,是致周、秦不相因,古今成間隔。自高祖至武帝,凡六世之前,盡竊遷書,不以為慚;自昭帝至平帝,凡六世,資于賈逵、劉韻,復不以為恥。況又有曹大家終篇,則固之自為書也幾希!往往出固之胸中者,《古今人表》耳,他人無此謬也。后世眾手修書,道傍筑室;掠人之文,竊鐘掩耳,皆固之作俑也。固之事業如此,后來史家奔走班固而不暇,何能測其深淺!遷之于固,如龍之于豬,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,劉知已之徒尊班而抑馬,且善學司馬遷者,莫如班彪。彪續遷書,自孝武至于后議,欲令后人之續已,如已之續遷;既無衍文,又無絕緒,世世相承,如出一手,善乎其繼志也,其書不可得而見。所可見者,元、成二帝贊耳。皆于本紀之外,別記所聞,可謂深入太史公之閫奧矣。
凡左氏之有“君子曰”者,皆經之新意;《史記》之有“太史公曰”者,皆史之外事,不為褒貶也。間有及褒貶者,褚先生之徒雜之耳。且紀傳之中,既載善惡,足為鑒戒,何必于紀傳之后更加褒貶?此乃諸生決科之文,安可施于著述?殆非遷、彪之意。況謂之贊,豈有貶辭?后之史家,或謂之“論”,或謂之“序”,或謂之“銓”,或謂之“評”,皆效班固,臣不得不劇論固也。司馬談有其書,而司馬遷能成其父志;班彪有其業,而班固不能讀父之書。固為彪之子,既不能保其身,又不能傳其業,又不能教其子,為人如此,安在乎言天下法!范曄、陳壽之徒繼踵,率皆輕薄無行,以速罪辜,安在乎筆削而為信史也!
孔子曰:“殷因于夏禮,所損益,可知也;周因于殷禮,所損益,可知也。”此言相因也。自班固斷代為史,無復相因之義,雖有仲尼之圣,亦莫知其損益,會通之道,自此失矣!語其同也,則紀而復紀,一帝而有數紀;傳而復傳,一人而有數傳。天文者,千古不易之象,而世世作《天文志》;《洪范五行》者,一家之書,而世世序《五行傳》。如此之類,豈勝繁文?語其異者,則前王不列于后王,后事不接于前事,郡縣各為區域,而昧遷革之源;禮樂自為更張,遂成殊俗之政。如此之類,豈勝斷綆!
曹、魏指吳、蜀為寇,北朝指東晉為僭;南謂北為索虜,北謂南為島夷。《齊史》稱梁軍為義軍,謀人之國可謂義乎?《隋書》稱唐兵為義兵,伐人之君可以為義乎?房玄齡董史冊,故房彥謙擅美名;虞世南預修書,故虞荔、虞寄有嘉傳。甚者,桀犬吠堯,吠非其主;《晉史》黨晉而不有魏,凡忠于魏者,目為叛臣,王凌、諸葛誕、毋邱儉之徒抱屈黃壤;《齊史》黨齊而不有宋,凡忠于宋者,目為逆黨,袁粲、劉秉、沈攸之之徒含冤九泉。噫!天日在上,安可如斯?似此之類,歷世有之。傷風敗義,莫大乎此!
遷法既失,固弊日深,自東都至江左,無一人能覺其非。惟梁武帝為此慨然,乃命吳均作《通史》,上自太初,下終齊室,書未成而均卒。隋楊素又奏令陸從典續《史記》訖于隋,書未成而免官。豈天之勒斯文而不傳與?抑非其人而不佑之與?自唐之后,又莫覺其非,凡秉史筆者,皆準《春秋》,專事褒貶。夫《春秋》以約文見義,若無傳釋,則善惡難明;史冊以詳文該事,善惡已彰,無待美刺。讀蕭、曹之行事,豈不知其忠良?見莽、卓之所為,豈不知其兇逆?夫史者,國之大典也,而當職之人,不知留意于憲章,徒相尚于言語,正猶當家之婦,不事饔飧,專鼓唇舌,縱然得勝,豈能肥家?此臣之所深恥也。
江淹有言:“修史之難,無出于志。”誠以志者,憲章所系,非老于典故者,不能為也。不比紀、傳,紀則以年系事,傳則以事系人,儒學之士皆能為之。惟有志難,其次如表,所以范曄、陳壽之徒能為紀、傳而不敢作表、志。志之大原,起于《爾雅》,司馬遷曰“書”,班固曰“志”,蔡邕曰“意”,華嶠曰“典”,張勃曰“錄”,何法盛曰“說”,余史并承班固,謂之“志”,皆詳于浮言,略于事實,不足以盡《爾雅》之義。臣今總天下學術而倏其綱目,名之曰“略”。凡二十略,百代之憲章,學者之能事,盡于此矣!其五略,漢、唐諸儒所得而聞;其十五略,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。
生民之本,在于姓氏;帝王之制,各有區分。男子稱氏,所以別貴賤;女子稱姓,所以別婚姻,不相紊濫。秦并六國,姓氏混而為一。自漢至唐,歷世有其書,而皆不明姓氏。原此一家之學,倡于左氏,因生賜姓,胙士命氏,又以字、以謚為官,以邑命氏,邑亦士也。左氏所言,惟茲五者。臣今所推,有三十二類,左氏不得有聞,故作《氏族略》。
書契之本,見于文字。獨體為文,合體為字。文有子母,主類為母,從類為子。凡為字書者,皆不識子母。文字之本,出于六書。象形,指事,文也;會意,諧聲,轉注,字也;假借者,文與字也。原此一家之學,亦倡于左氏。然止戈為武,不識諧聲;反正為乏,又昧象形。左氏既不別其源,后人何能別其流?是致小學一家,皆成鹵莽。經旨不明,穿鑿蜂起,盡由于此。臣于是驅天下文字盡歸六書。軍律既明,士乃用命,故作《六書略》。
天籟之本,自成經緯。縱有四聲以成經,橫有七音以成緯。皇頡制字,深達此機;江左四聲,反沒其旨。凡為韻書者,皆有經無緯。字書眼學,韻書耳學。眼學以母為主,耳學以子為主。母主形,子主聲,二家俱失所主。今欲明七音之本,擴六合之情,然后能宣仲尼之教,以及人間之俗,使裔夷之俘皆知禮,故作《七音略》。
天文之家,在于圖象。民事必本于時,時序必本于天。為天文志者,有義無象,莫能知天。臣今取隋丹元子《步天歌》,句中有圖,言下成象;靈臺所用,可以仰觀。不取甘石本經,惑人以妖妄,速人于罪累,故作《天文略》。
地理之家,在于封圻。而封圻之要,在于山川。《禹貢》九洲,皆以山川定其經界。九洲有時而移,山川千古不易,是故《禹貢》之圖,至今可別。班固《地理》主于郡國,無所底止,雖有其書,不如無也。后之史氏,正以方隅;郡國并遷,方偶顛錯,皆因司馬遷無地理書,班固為之創始,至此一家,俱成謬舉。臣今準《禹貢》之書而理川源,本《開元十道圖》,以續古今,故作《地理略》。
都邑之本,金湯之業。史氏不書,《黃圖》難考。臣上稽三皇、五帝之形勢,遠探四夷、八蠻之巢穴,仍以梁汴者,四朝舊都,為痛定之戒;南陽者,疑若可為中原之新宅,故作《都邑略》。
謚法一家,國之大典。史氏無其書,奉常失其旨。周人以諱事神,謚法之所由起也。古之帝王,存亡皆用名。自堯、舜、禹、湯至于桀、紂,皆名也。周公制禮,不忍名其先君;武王受命后,乃追謚太王、王季、文王,此謚法所由立也。本無其書,后世偽作周公謚法,欲以生前之善惡,為死后之勸懲。且周公之意,既不忍稱其名,豈忍稱其惡?如是,則《春秋》為尊者諱,不可行乎周公矣,此不道之言也。幽、厲、恒靈之字,本無兇義,謚法欲名其惡,則引辭以遷就其意。何為皇額制字,使字與義合,而周公作法,使字與義離?臣今所纂,并以一字見義,削去引辭,而除其曲說,故作《謚法》。
祭器者,古人飲食之器也。今之祭器,出于禮圖,徒務說義,不思適用。形制既乘,豈便歆享?夫祭器尚象者,古之道也。器之大者如罍,故取諸云、山;其次莫如尊,故取諸牛、象;其次莫如彝,故取諸雞、鳳;最小者莫如爵,故取諸雀。其制皆象其形,鑿項及背以出內酒。惟劉杳能說其義,故引魯郡地中所得齊子尾送女器有“犧尊”及齊景公家書所得“牛尊”、“象尊”以為證,其義甚明,世莫能用。故作《器服略》。
樂以詩為本,詩以聲為用。風土之音曰“風”,朝廷之音曰“雅”,宗廟之音曰“頌”。仲尼編《詩》,為正樂也。以風雅頌之歌,為燕享祭祀之樂。工歌《鹿鳴》之三,笙吹《南陔》之三,歌間《魚麗》之三,笙間《崇邱》之三,此大合樂之道。古者絲竹有譜無辭,所以六笙但存其名。序《詩》之人,不知此理,謂之有其義而亡其辭。良由漢立齊、魯、韓、毛四家博士,各以義言《詩》,遂使聲歌之道微。至后漢之末,《詩》三百僅能傳《鹿鳴》《騶虞》《伐檀》《文王》四篇之聲而已。太和末,又失其三,至晉室,《鹿嗚》一篇又無傳。自《鹿鳴》不傳,后世不復聞詩。然詩者,人心之樂也,不以世之興衰而存亡。繼風、雅之作者,樂府也。史家不明仲尼之意,棄樂府不收,乃取工伎之作以為志。臣舊作《系聲樂府》以集漢魏之辭,正為此也。今取篇目以為次,曰樂府正聲者,所以明風、雅;曰祀享正聲者,所以明頌。又以琴操明絲竹,以遺聲準逸詩。語曰:“'韶’,盡美矣,又盡善也;'武’,盡美矣,未盡善也”。此仲尼所以正舞也。“韶”即文舞,“武”即武舞。古樂甚希,而文、武二舞猶傳于后世。良由有節而無辭,不為以說家所惑,故得全仲尼之意。五聲、八音,十二律者,樂之制也,故作《樂略》。
學術之茍且,由源流之不分。書籍之散亡,由編次之無紀。《易》雖一書,而有十六種學:有傳學,有注學,有章句學,有圖學,有數學,有讖緯學,總得總言《易》類乎?《詩》雖一書,而有十二種學:有詁訓學,有傳學,有注學,有圖學,有譜學,有名物學,總得總言《詩》類乎?道家則有道書,有道經,有科儀,有符篆,有吐納丹田,有爐火外丹,凡二十五種,皆道家,而渾為一家,可乎?醫方則有脈經,有灸經,有本草,有方書,有炮炙,有病源,有婦人,有小兒,凡二十六種,皆醫家,而渾為一家,可乎?故作《藝文略》。
冊府之藏,不患無書;校讎之司,未聞其法。欲三館無素餐之人,四庫無蠹魚之簡,千章萬卷,日見流通,故作《校讎略》。
河出《圖》,天地有自然之象,圖譜之學由此而興;洛出《書》,天地有自然之文,書籍之學由此而出。圖成經,書成緯,一經一緯,錯綜而成文。古之學者,左圖右書,不可偏廢。劉氏作《七略》,收書不收圖;班固即其書為《藝文志》。自此以還,圖譜日亡,書籍日冗,所以困后學而墜良材者,皆由于此。何哉?即圖而求易;即書而求難。舍易從難,成功者少。臣乃立書二記:一曰記有,記今之所有者,不可不聚;二曰記無,記今所無者,不可不求。故作《圖譜略》。
方冊者,古人之言語;款識者,古人之貌。方冊所載,經數千萬傳;款識所勒,猶存其舊。蓋金石之功,寒暑不變,以茲稽古,庶不失真。今藝文有志,而金石無紀。臣于是采三皇五帝之泉幣,三王之鼎彝,秦人之石鼓,漢魏之豐碑。上自蒼頡石室之文,下逮唐人之書,各列其人而名其地,故作《金石略》。
《洪范五行傳》者,巫瞽之學也。歷代史官皆本之以作五行志。天地之間,災祥萬種;人間禍福,冥不可知,若之何一蟲之妖,一物之戾,皆繩之于五行!又若之何晉厲公一視之遠,周單子一言之徐,而能關于五行之沴乎?晉申公一衣之偏,鄭子臧一冠之異,而能關于五行之沴乎?董仲舒以陰陽之學,倡以此說,本于《春秋》,牽和附會。歷代史官,自愚其心目,俯首以受籠罩而欺天下。臣故削去五行,而作《災祥略》。
語言之理易推,名物之狀難識。農圃之人識田野之物,而不達《詩》《書》之旨;儒生達《詩》《書》之旨,而不識田野之物。五方之名本殊,萬物之形不一,必廣覽動植,洞見幽潛,通鳥獸之情狀,察草本之精神,然后參之載籍,明其品匯,故作《昆蟲草木略》。
凡十五略,出臣胸臆,不涉漢、唐諸儒議論。《禮略》所以敘五禮,《職官略》所以秩百官,《選舉略》言掄材方,《刑法略》言用刑之術,《食貨略》言財貨之源流,凡茲五略,雖本前人之典,亦非諸史之文也。
古者記事之史謂之志。《書大傳》曰:“天子有問無對,責之疑;有志而不志,責之丞。”是以宋、鄭之史,皆謂之志。太史公更志為記,今謂之志,本其舊也。桓君山曰:“太史公《三代世表》旁行邪上,并效《周譜》。”古者紀年別系之書謂之譜,太史公改而為表,今復表為譜,率從舊也。然西周經幽王之亂,紀載無傳,故《春秋》編年以東周為始。自皇甫謐作《帝王世紀》及《年歷》,上極三皇,譙周、陶弘景之徒,皆有其書。學者疑之,而以太史公編年為正,故其年始于共和。然共和之名,已不可據,況其年乎?仲尼著書,斷自唐、虞,而紀年始于魯隱,以西周之年無所考也。今之所譜,自《春秋》前稱世,謂之世譜;《春秋》之后稱年,謂之年譜。太史公紀年以六甲,后之紀年者以六十甲,或不用六十甲而用歲陰、歲陽之名。今之所譜,即太史公法,既簡且明,循環無滯。禮言臨文不諱,謂私諱不可施之于公也。若廟諱,則無所不避。自漢、唐,史官皆避諱,惟《新唐書》無所避。臣今所修,準舊例,間有不得而避者,如謚法之類,改易本字,則其義不行,故亦唐舊(漢景帝名啟,改啟為開;安帝名慶,改慶為賀;唐太祖名虎,改虎為武;高祖名淵,改淵為水。若章懷太子注《后漢書》,則濯龍淵不得而為諱;杜佑作《通典》,則虎賁不得而諱)。
夫學術超詣,本乎心識,如人入海,一人一深。臣之二十略,皆臣自有所得,不用舊史之文。紀傳者,編年紀事之實跡,自有成規,不為智而增,不為愚而減,故于紀傳即其舊文,從而損益。若紀有詔之辭,傳書有疏之章,入之為書,則據實事;慎之別錄,則見類例。《唐書》、《五代史》皆本朝大臣所修,微臣所不敢議,故紀傳訖隋。若禮樂政刑,務存因革,故引而至唐云。
嗚呼!酒醴之未,自然澆漓;學術之末,自然淺近;九流設教,至未皆弊。然他教之弊,惟在典刑;惟儒一家,去本太遠。此理何由?班固有言:“自武帝立五經博士,開第子員,設科射策,勸以官祿,訖于元始,百有余年。傳業者寢盛,枝葉繁滋,一經說至百余萬言,大師眾至千余人,蓋祿利之路然也。”且百年之間,其患如此;千載之后,弊將若何?況祿利之路,必由科目;科目之設,必由乎文辭。三百篇之《詩》,盡在聲歌,自置《詩》博士以來,學者不聞一篇之《詩》;六十四卦之《易》,該于象數,自置《易》博士以來,學者不見一卦之《易》。皇頡制字,盡由六書,漢立小學,凡文字之家,不明一字之宗。伶倫制律,盡本七音;江左置聲韻,凡音律一家,不達一音之旨。經既茍且,史又荒唐,如此流離,何時返本?道于污隆存乎時,時之通塞存乎數,儒學之弊,至此而極!寒極則暑來,否極則泰來,此自然之道也。臣蒲柳之質,無復余齡,蔡藿之心,惟期盛世!謹序
予初游潭上,自旱西門左行城陰下,蘆葦成洲,隙中露潭影。七夕再來,又見城端柳窮為竹,竹窮皆蘆,蘆青青達于園林。后五日,獻孺召焉。止生坐森閣未歸,潘子景升、鐘子伯敬由蘆洲來,予與林氏兄弟由華林園、謝公墩取微徑南來,皆會于潭上。潭上者,有靈應,觀之。
岡合陂陀,木杪之水墜于潭。清涼一帶,坐灌其后,與潭邊人家檐溜溝勺入浚潭中,冬夏一深。閣去潭雖三丈余,若在潭中立;筏行潭無所不之,反若往水軒。潭以北,蓮葉未敗,方作秋香氣,令筏先就之。又愛隔岸林木,有朱垣點深翠中,令筏泊之。初上蒙翳,忽復得路,登登至岡。岡外野疇方塘,遠湖近圃。宋子指謂予曰:“此中深可住。若岡下結廬,辟一上山徑,頫空杳之潭,收前后之綠,天下升平,老此無憾矣!”已而茅子至,又以告茅子。
是時殘陽接月,晚霞四起,朱光下射,水地霞天。始猶紅洲邊,已而潭左方紅,已而紅在蓮葉下起,已而盡潭皆頳。明霞作底,五色忽復雜之。下岡尋筏,月已待我半潭。乃回篙泊新亭柳下,看月浮波際,金光數十道,如七夕電影,柳絲垂垂拜月。無論明宵,諸君試思前番風雨乎?相與上閣,周望不去。適有燈起薈蔚中,殊可愛。或曰:“此漁燈也。”
大哉乾象,紫微疏上帝之宮;邈矣坤輿,丹闕披圣人之宇。聿觀文而聽政,宜配天而宗祖;體神化以成規,應靈圖而立矩;度七筵以垂憲,分四室而通輔。合宮之典,郁乎軒邱;重屋之儀,崇於夏禹。因殷成於五帝,繼周道於千古。統正朔之相循,起皇王之踵武。大禮興而三靈洽,至道融而萬物睹,其在國乎?
惟圣踐極,配永登樞。浹生成於大冶,銷品匯於洪爐。貫星象而調七政,列山川而宅五都。開洛陽之寶籍,受河闕之禎圖。總夔龍於國序,集?鷺於天衢,包壯業於元頊,籠景化於黃虞。功既成矣,道既貞矣。答后土之嘉祥,藹上元之殊祉;望仙閣之秀出,瞻月觀之宏峙;鏤紅玉以圖芳,肅龜壇而薦祀;道不言而有洽,物無為而自致。向明南面,高居北辰。屬天下之同軌,率海內以嚴?,想?臺以應物,考明堂以臨人。協和萬?,懷柔百神。降虔心,啟靈術,采舊典,詢故實。表至德於吹萬,起宏規於太一。欣作之於有范,佇成之於不日。
工以奔競,人皆樂康。訪子輿於前跡,揆公玉之遺芳;順春秋之左右,法天地之圓方。成八風而統刑德,觀四序而候炎涼;跨東西而作甸,掩二七以疏疆。下臨星雨,傍控煙霜。翔軍?墜於層極,宛虹拖於游梁。昆山之玉樓偃蹇,曾何仿佛;滄海之銀宮煥爛,安足翱翔?
于是覽時則,徵月令,觀百王,綏萬姓。肆類之典攸集,郊?之禮爰盛。衣冠肅於虔誠,禮樂崇於景令。三陽再啟,百辟來朝,元?霧集,旌旆?搖。湛恩畢被,元氣斯調,羅九賓之玉帛,舞六代之咸韶。澤被翔泳,慶溢煙霄。穆穆焉,皇皇焉,粵自開辟,未有若斯之壯觀者矣!煥乎王道,昭賁三才,遠乎圣懷,周流九垓。鴻名齊於太昊,茂實光乎帝魁。浹群山於雨露,通庶品以風雷。盛矣美矣!皇哉,唐哉!
珠箔隔輕寒,鸚鵡玲瓏語。悄喚鎖重門,莫放春歸去。
桃李可憐生,各自啼紅雨。點點帶愁飄,吹入春江住。
河西老卒不知秋,獨倚營門望戍樓。蘆管聲中千里月,萬行征淚一時流。
江靜復川明,榮光滿帝京。是日年祥發,皚皚飛素雪。
繽紛素雪應祈興,慘淡玄陰萬里凝。瑟瑟初看先集霰,峨峨旋見已成冰。
輕飛急灑亂霏霏,楚水吳山尤自宜。大路樓臺爭改色,層城宮闕轉生姿。
翻時似浣紅塵陌,舞處偏迷白玉墀。凌空遙曳雜風飄,委谷填丘積不消。
昔望兼時將度歲,今看合夜并連朝。為慶經冬方入地,誰言上世不封條。
睹瑞歡歌何所致,春卿秉禮崇禋祀。同云聚景禱前生,赤日韜光齋后避。
共言六律失天司,賴有秩宗能感帝。秩宗美德合純精,并操聯輝雪比清。
姑圣相逢曾問道,海神出見盡知名。如鹽持調商家鼎,愿糝梅實作和羹。
美酒斗十千。更對花前。芳樽肯放手中閒。起舞酬花花不語,似解人憐。
不醉莫言還。請看枝閒。已飄一片減嬋娟。花落明年猶自好,可惜朱顏。
南風其徐大火流,飛鴻鳴鳥聲相求。勸君置節且莫嘆,聽我撫觴歌壯游。
六轡如絲子所持,壯游萬里自茲始。圣皇穆穆開虞聰,昭代濟濟崇周禮。
天明地察隆祀典,睦族展親敦令豈。玉牒千年奉至尊,金章八道馳行使。
黃封朝下明光宮,輶軒夕度瀘溝水。益州鳥道接秦川,隴坂緣云高插天。
辨方藩肇蠶叢域,經野星分井鬼躔。駟馬橋連清渭曲,太白標絕峨眉顛。
洶淙巖石互蕩潏,懸梯斷棧相鉤連。丞相廟深老柏裂,子云亭古蒼苔芊。
此去先登泰華峰,巨靈屃赑與天通。滄波夜瀉魚龍靜,薜荔秋封鳥鼠空。
百年關頭長濤浪,九折盤西多雨風。始信猿聲墮客淚,遙憐巴唱引行艟。
皇皇帝命遐荒歡,朱門香裊輕煙寒。捧詔日高紫氣繞,上殿風引鳴珂珊。
蜀王秉禮拜手讀,溪老喧呼扶杖看。過秦論擬觀風著,劍閣銘應覽勝刊。
回舟好過滟滪堆,巫峽秋濤日夜來。瀟湘竹密湖光動,濯錦帆張江色開。
作賦還投汨羅畔,題詩許上望鄉臺。蒼梧氣遠不可叫,白帝城孤空自哀。
君不見成都當時羨相如,諭蜀文高輝駟車。子長歷覽浮湘水,歸來乃有石室居。
故知壯士之志在四方,睢睢盱盱,戶庭不出非丈夫。
方塘子,自矜意氣彌宇宙。天路云逵不足登,要使聲華滿人口。
秖今天子勤延佇,持歸報答何所有。去住萍蹤豈足知,我歌壯游君莫疑。
今我忽兮不樂,駕言游兮名山。陟巖岫兮崆嵑,躡絕頂兮?岏。
煙霏霏兮云在下,信斯美兮非人寰。山中之人兮冰雪顏,沆瀣飲兮瓊膏餐。
神炯炯兮霍耀,膚綽約兮流素丹。糝瑤蕊兮翳文芝,餌五術兮佩華菅。
駟玉虬兮馭鳧鹥,鳳凰翼蓋兮翔文鸞。宓妃嬋媛兮后乘豐隆,屏翳兮郁以承鑾。
紛飄飖兮下御,倏往來兮山之間。辟天閽兮延予,啟玉粲兮嫣然。
導予兮元秘,授予兮靈詮。揖洪厓兮為侶,快執袂兮偓佺。
朅浩蕩兮高舉,極玄圃兮閬顛。超溟涬兮若視,遺龍蠖兮空筌。
先生大隱者,在世自如遺。樂道尚玄白,持心不磷緇。
閒門無客候,幽幌對花垂。好我忘年少,但言相見遲。
漢將標南紀,周王暨外埏。黃支開象郡,赤社直牛纏。
濰水扶桑表,郁林滄海邊。霜清八桂瘴,嵐結九疑煙。
立壁攢青蓋,飛峰削紫蓮。伏波盤荔峽,羅閣瞰梧川。
光色美如此,珍奇產固然。軌苞輸御府,貢篚達郊廛。
經野襟交廣,肇封俯柳全。授圭羅赭組,分土胙炎天。
玉葉枝璀璨,銀潢派接連。維城宗子令,開國大君專。
帶礪河山固,金湯磐石堅。瞻依一萬里,屏翰二千年。
惇族紆宸眷,建侯展睿權。文閶簇仗啟,廣樂鼓鏞闐。
貝闕丹霞裊,銅樓霽景鮮。冠裳趨濟濟,纓??萃翾翾。
節捧星辰上,制傳象緯前。瑤函藏寶冊,金匱閟琳編。
翠琯祥云抱,紫泥卿日懸。皇華十道出,司諫一身遷。
螭筆暫須輟,龍顏夢尚牽。蘭坰張祖晏,桐柱奏離弦。
雪送燕關騎,春催楚蠡船。異花紛拂?,怪鳥噦迎旃。
廬霍行堪結,巫衡覽更便。槎搖弱水影,旌飏閬風顛。
列洞密猩語,諸蠻解漢言。岡巒眺邈邈,原薄驟駪駪。
篁竹啼猿合,石楠蹻??緣。輶軒駢入境,劍舄忽登仙。
圣主威光近,明王禮數虔。遐荒憲命播,藩域寵靈宣。
晝向日邊接,昏從花下旋。墀迎珠躡履,裾曳??平氈。
淮國宴游洽,梁園詞藻傳。觀風行問俗,訪古重懷賢。
帝子蒼梧些,湘妃澧浦篇。堯山澆桂酒,舜廟擷芳筌。
逢鶴還珠洞,尋砂勾漏泉。豈云奔命遠,宜是勝游偏。
謝客唫應遍,仲宣賦可鐫。茫茫五嶺外,何日使星還。
輕舟恣所往,適趣何必深。居然在城郭,而得混魚禽。
翠岫遠銜席,綠波清照襟。明湖既得性,芳歲亦娛心。
暮景媚涵水,春風吹滿林。岸木稍變色,汀草微生陰。
浩蕩紛言笑,滿盈遞酌斟。不能日日至,勿云樂太湛。
此曲之作,有自來矣。昔胡元大都妓女名莘文秀者,美姿色,與學士王元鼎有姻,亦與阿魯相契。異期阿與莘仵坐,談及風情之任。阿曰:“聞爾與王元鼎情思甚篤,以予方之,孰最?”莘含笑不語,阿強之再四。莘曰:“以調和鼎鼐,燮理陰陽,則學士不如丞相;論惜玉憐香,嘲風詠月,則丞相少次于學士。”哄然一笑而罷。元鼎聞之,故作此以嘲之。
走將來涎涎瞪瞪冷眼兒[目岑],杓杓答答熱句兒浸。舍不的纏頭錦,心疼的買笑金,要你消任。鴛幃珊枕,鳳凰杯悲翠衾。低低唱,淺淺斟,休逞波李翰林。
【幺篇】支楞、弦斷了綠綺琴,[王吉]玎、掂折了碧玉簪。嗨,墮落了題橋志;吁,闌珊了解佩心。走將來笑吟吟,妝呆妝婪,硬廝掙,軟廝禁;泥中刺,綿里針;黑頭蟲,黃口[岑鳥]。
【鳳鸞吟】自古到今,恩多須怨深。你說的牙疼誓,不害磣!有酒時唫,有飯時啃,你來我根前委實圖甚?小的每聲價兒[亻些],身材兒婪,請先生別覓個知音。
【柳葉兒】走將來乜斜頭撒唚,不熨貼性兒希林,軟處捏,硬處搊,甜處滲。休忒恁,莫沉吟,休辜負了柳影花陰。
十年鴻雪邗江住,相逢選樓樓下。小字珠含,芳姿玉映,佳婿乘龍來迓。
青琴調寡。是韋貫紅妝,擘弦能亞。詠絮吟成,韻流松石古池榭。
鄉關旋警燕幕,小村同避地,睽隔茅舍。靜樹烏啼,寒潮鯉訊,難慰椒窗晨夜。
鸞笙去也。嘆一霎罡風,頓蔫桃帕。漫展瑤編,麝丸和淚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