瀛臺侍直七月至九月得十六首 其四
樓臺樹石水中央,聯(lián)句何年踵柏梁?宿衛(wèi)廬虛橋板在,忍從老監(jiān)說先皇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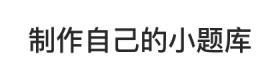
樓臺樹石水中央,聯(lián)句何年踵柏梁?宿衛(wèi)廬虛橋板在,忍從老監(jiān)說先皇?
春日春風春景媚。春山春谷流春水。春草春花開滿地。乘春勢。百禽弄古爭春意。澤又如膏田又美。禁煙時節(jié)堪游戲。正好花間連夜醉。無愁系。玉山任倒和衣睡。
山中好,最好是春時。紅白野花千種樣,間關幽鳥百般啼。空翠濕人衣。 茶自采,筍蕨更同薇。百結布衫忘世慮,幾壺村酒適天機。一醉任東西。
一團膿,三寸氣。使作還同傀儡。夸體段,騁風流。人人不肯休。白玉肌,紅粉臉。盡是浮華妝點。皮肉爛,血津乾。荒郊你試看。
七盤一何高,蒼翠凈寥廊。 夜雨濯杉檜,春風散芝藥。 細云散巖色,細逕度危筰。 邑改井已泥,空余漢城郭。 土瘠漫生茶,人稀時走玃。 苔蘚囹圄空。塵埃簿書合。 縣圃何蕭條,半櫻半零落。 偃蹇大夫松,委蛇君子鶴。 試登三友堂,借問何人作。 皆云楊先生,好詩心淡泊。 乘興山水間,此君供獻酢。 瑯玕無俗韻,仁智有真樂。 取友信可人,自待宜不薄。 我來宴坐久,寂寥無唯諾。 明月來徘徊,清風自蕭縈。 因留風與月,相對成清酌。 蟾光照金尊,余輝射杯酒。 輕飔入朱弦,彷佛奏簫勺。 醺然造忘形,神交通博約。 醉號五賢堂,醒來資一噱。
人在年少,神情未定,所與款狎,熏漬陶染,言笑舉動,無心于學,潛移暗化,自然似之。何況操履藝能,較明易習者也?是以與善人居,如入芝蘭之室,久而自芳也;與惡人居,如入鮑魚之肆,久而自臭也。《顏氏家訓》
古之學者為己,以補不足也;今之學者為人,但能說之也。古之學者為人,行道以利世也;今之學者為己,修身以求進也。夫學者猶種樹也,春玩其華,秋登其實;講論文章,春華也,修身利行,秋實也。《顏氏家訓》
學之所知,施無不達。世人讀書者,但能言之,不能行之,忠孝無聞,仁義不足;加以斷一條訟,不必得其理;宰千戶縣,不必理其民;問其造屋,不必知楣橫而悅豎也;問其為田,不必知稷早而黍遲也;吟嘯談謔,諷詠辭賦,事既優(yōu)閑,材增迂誕,軍國經綸,略無施用;故為武人俗吏所共嗤詆,良由是乎?
夫學者所以求益耳。見人讀數(shù)十卷書,便自高大,凌忽長者,輕慢同列;人疾之如仇敵,惡之如鴟梟。如此以學自損,不如無學也。
古之學者為己,以補不足也;今之學者為人,但能說之也。古之學者為人,行道以利世也;今之學者為己,修身以求進也。夫學者猶種樹也,春玩其華,秋登其實;講論文章,春華也,修身利行,秋實也。
齊朝有一士大夫,嘗謂吾曰:“我有一兒,年已十七,頗曉書疏。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,以此伏事公卿,無不寵愛,亦要事也。”吾時睥倪而不答。異哉,此人之教子也!若由此業(yè),自致卿相,亦不愿汝曹為之。
邂逅溪源一夢中,空余羅袖疊春叢。 生憐煙杏勻肌薄,不分江梅映肉紅。 要識臨塘比西子,便須索酒對東風。 隨君拄杖敲門去,莫惜觥船一棹空。
曉鶯聲里。睡思酣猶美。旖旎紅娘冰雪體。洛女巫娥浮靡。紫騮踏月嘶風。華裾織翠青蔥。歸去一場春夢,空吟舊綠新紅。
分得藩符近海濱,溪山清處養(yǎng)天真。 幅巾隱幾春菴靜,直是義皇已上人。
倉卒蠻鼙上水濱,使君忠憤獨亡身。 平明戈劍摧城闔,俄頃衣冠落路塵。 志士一門能許國,老夫當日亦知人。 朝廷贈禭哀榮極,青骨千金合有神。
人生七十,都道是、自古世間稀有。今日華堂,阿彌初度,更綿綿增壽。花柳呈妍香云靄,正好暮春時候。江山如畫,百年風景依舊。最喜蘭玉森森,彩衣齊拜,舞塤*迭奏。羅綺香中蟠桃熟,爭獻瑤池王母。愧忝姻聯(lián)倚莊椿,瓊樹歲寒長久。歌詞一闋,敬稱千歲春酒。
巢父者,堯時隱人也。山居不營世利,年老以樹為巢,而寢其上,故時人號曰巢父。堯之讓許由也,由以告巢父,巢父曰:“汝何不隱汝形,藏汝光,若非吾友也!”擊其膺而下之,由悵然不自得。乃過清泠之水,洗其耳,拭其目,曰:“向聞貪言,負吾之友矣!”遂去,終身不相見。
許由,字武仲,堯聞致天下而讓焉,乃退而遁于中岳穎水之陽,箕山之下隱。堯又召為九州長,由不欲聞之,洗耳于穎水濱。時有巢父牽牛欲飲之,見由洗耳,問其故。對曰:“堯欲召我為九州長,惡聞其聲,是故洗耳。”巢父曰:“子若處高岸深谷,人道不通,誰能見子?子故浮游,欲聞求其名譽,污我犢口!”牽牛上流飲之。《高士傳》
夏馥字子治,陳留圉人也。少為諸生,質直不茍,動必依道。同縣高儉及蔡氏,凡二家豪富,郡人畏事之,唯馥閉門不與高、蔡通。桓帝即位,災異數(shù)發(fā),詔百司舉直言之士各一人。太尉趙戒舉馥,不詣,遂隱身久之。靈帝即位,中常侍曹節(jié)等專朝,禁錮善士,謂之黨人。馥雖不交時官,然聲名為節(jié)等所憚,遂與汝南范滂、山陽張儉等數(shù)百人并為節(jié)所誣,悉在黨中。詔下郡縣,各捕以為黨魁。馥乃頓足而嘆曰:“孽自已作,空污良善。一人逃死,禍及萬家,何以生為?”乃自翦須,變服易形入林慮山中,為冶工客作,形貌毀悴,積傭三年,而無知者。后詔委放,儉等皆出,馥獨嘆曰:“已為人所棄,不宜復齒鄉(xiāng)里矣!”留賃作不歸,家人求不知處。其后,人有識其聲者,以告同郡止鄉(xiāng)太守濮陽潛,使人以車迎馥,馥自匿不肯,潛車三返,乃得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