望梅
朱明開席。正荷香十里,槐陰千尺。向風亭、卷起湘簾,好箕踞科頭,納涼留客。
河朔風流,每避暑、杯盤狼藉。況歌翻水調,冰貯玉壺,微聞香澤。
佳人素妝瑩白。看醉眠如畫,紗櫥籠碧。賽廣寒宮里嬋娟,喜瑣闥南有、銀蟾流魄。
夢醒巫山,驟雨過、陂塘蕭索。更移尊痛飲,高枕云溪永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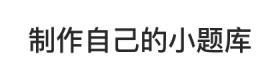
朱明開席。正荷香十里,槐陰千尺。向風亭、卷起湘簾,好箕踞科頭,納涼留客。
河朔風流,每避暑、杯盤狼藉。況歌翻水調,冰貯玉壺,微聞香澤。
佳人素妝瑩白。看醉眠如畫,紗櫥籠碧。賽廣寒宮里嬋娟,喜瑣闥南有、銀蟾流魄。
夢醒巫山,驟雨過、陂塘蕭索。更移尊痛飲,高枕云溪永夕。
盛夏時節擺開宴席。此時十里荷塘飄著荷香,槐樹投下千尺濃蔭。在臨風的亭中,卷起湘簾,我隨意地敞著頭巾、伸開兩腿坐著,留客一起納涼。我們有著河朔名士的風流,每到避暑時,杯盤雜亂。況且歌聲翻著《水調》曲,玉壺里藏著寒冰,還微微能聞到美人的香氣。佳人素妝,肌膚瑩白。看她醉眠的樣子如畫一般,被碧紗櫥籠罩著。她賽過廣寒宮里的嫦娥,可喜的是南窗有明月流瀉清光。從巫山美夢中醒來,驟雨過后,池塘一片蕭索。于是再移動酒杯痛飲,在云溪邊高枕安眠直至天亮。
朱明:夏季。
箕踞科頭:箕踞,伸開兩腿坐著,是一種不拘禮節的坐姿;科頭,不戴帽子,裸露著頭。
河朔風流:指三國時袁紹的賓客在河朔避暑宴飲的風流雅事。
水調:曲調名。
瑣闥:刻有連瑣圖案的宮中小門,這里指窗戶。
銀蟾:月亮。
巫山:用宋玉《高唐賦》中楚王夢與巫山神女相會的典故。
陂塘:池塘。
移尊:移動酒杯,指繼續飲酒。
具體創作時間和地點難以確切考證。從詞的內容推測,可能創作于夏日,詞人在舒適的環境中與友人宴飲納涼,觸景生情而作。當時社會環境若處于和平時期,人們有閑暇享受生活,詞人便以詞記錄下這份愜意。
這首詞主旨是描繪夏日納涼的生活場景,展現了詞人的閑適生活。其特點是意象豐富、意境優美、語言典雅,運用典故增添韻味。在文學史上雖可能不是廣為人知的名篇,但也體現了詞人的創作才華和當時的生活情趣。
深閨悄。葉落梧桐秋欲老。攬鏡愁多少。闌干憑遍西風掃。
情渺渺。試問菊花期,還是霜前好。
浮云漠漠草離離,淚濕春衫鬢腳垂。秋水為神玉為骨,芙蓉如面柳如眉。 鐘隨野艇回孤棹,蟬曳殘聲過別枝。青冢路邊南雁盡,問君何事到天涯。
與君別約記杭州,山外青山樓外樓。 屈指別來今幾載,愁心一倍長離憂。
青陽播林麓,百卉生光妍。 如何空谷資,尚爾霜霰纏。 守節抱苦貞,豈不幽且寒。 由來松柏性,羞學桃李顏。
金吾持戟護軒檐,天樂傳教萬姓瞻。 樓上美人相倚看,紅妝透出水晶簾。 玉樓天半起笙歌,風送宮人笑語和。 月影殿開聞曉漏,水晶簾卷近秋河。
青山隱隱水迢迢,客夢都隨歲月消。 惟有別時今不忘,水邊楊柳赤闌橋。
輔贊藏諸用,庸人自擾之。 惟公知好靜,與物盡忘私。 德望儀群辟,威名憺遠夷。 傷心白雞夢,梁木有余悲。
茫茫。蒼蒼。青山繞、千頃波光。新秋露風荷吹香。悠颺心地然,生清涼。古岸搖垂楊。時有白鷺飛來雙。隱君如在,鶴與翱翔。老仙何處,尚有流風未忘。琴與君兮宮商。酒與君兮杯觴。清歡殊未央。西山忽斜陽。欲去且徜徉。更將霜鬢臨滄浪。
半野園者,故相國陳公說巖先生之別墅也。相國既沒,距今十有余年,園已廢為他室。而其中花木之薈萃,足以誤日;欄檻之回曲,足以卻暑雨而生清風;樓閣之高迥,足以挹西山之爽氣,如相國在時也。
庚戌之春,余友杭君大宗來京師,寓居其中。余數過從杭君,圍以識半野園之概。而是時,杭君之鄉人有陳君者,亦寓居于此。已而陳君將之官粵西,顧不能意情此園,令工畫者為圖,而介杭君請余文以為之記。
夫天下之山水,攢蹙累積于東南,而京師車馬塵囂,客游者往往縈紆郁悶,不能無故土之感。陳君家杭州,西子湖之勝甲于天下。舍之而來京師,宜其有不屑于是園者;而低徊留連之至不忍以去,則陳君于為官,其必有異于俗吏之為之己。雖然,士當貧賤,居陋巷,甕牖繩樞自足也;間至富貴之家,見樓閣欄檻花木之美,心悅而慕之。一日得志,思以逞其欲,遂至脧民之生而不顧,此何異攻摽劫奪之為者乎?然則,陳君其慕為相國之業而無慕乎其為國,可也!
泠然。清圓。誰彈。向屋山。何言。清風至陰德之天。悠颺馀響嬋娟。方晝眠。迥立八風前。八音相宣知孰賢。有時悲壯,鏗若龍泉。有時幽杳,彷佛猿吟鶴怨。忽若巍巍山巔。蕩蕩幾如流川。聊將娛暮年。聽之身欲仙。弦索滿人間。未有逸韻如此弦。
乘騎者皆賤騾而貴馬。夫煦之以恩,任其然而不然,迫之以威使之然,而不得不然者,世之所謂賤者也。煦之以恩,任其然而然,迫之以威使之然而愈不然,行止出于其心,而堅不可拔者,世之所謂貴者也,然則馬賤而騾貴矣。雖然,今夫軼之而不善,榎楚以威之而可以入于善者,非人耶人豈賤于騾哉?然則騾之剛愎自用,而自以為不屈也久矣。嗚呼!此騾之所以賤于馬歟?
先大父側室,姓章氏,明崇禎丙子十一月二十七日生。年十八來歸,逾年,生女子一人,不育。又十余年,而大父卒。先大母錢氏。大母早歲無子,大父因娶章大家。三年,大母生吾父,而章大家卒無出。大家生寒族,年少,又無出,及大父卒,家人趣之使行,大家則慷慨號慟不食。時吾父才八歲,童然在側,大家挽吾父跪大母前,泣曰:“妾即去,如此小弱何?”大母曰:“若能志夫子之志,亦吾所荷也。”于是與大母同處四十余年,年八十一而卒。
大家事大母盡禮,大母亦善遇之,終身無間言。櫆幼時,猶及事大母。值清夜,大母倚簾帷坐,櫆侍在側,大母念往事,忽淚落。櫆見大母垂淚,問何故,大母嘆曰:“予不幸,汝祖中道棄予,汝祖沒時,汝父才八歲。”回首見章大家在室,因指謂櫆曰:“汝父幼孤,以養以誨,俾至成人,以得有今日,章大家之力為多。汝年及長,則必無忘章大家。”時雖稚昧,見言之哀,亦知從旁泣。
大家自大父卒,遂表明。目雖無見,而操作不輟,槐七歲,與伯兄、仲兄從塾師在外庭讀書。每隆冬,陰風積雪,或夜分始歸,僮奴皆睡去,獨大家煨爐以待。聞叩門,即應聲策杖扶壁行,啟門,且執手問曰:“書若熟否?先生曾樸責否?”即應以書熟,未曾樸責,乃喜。
大家垂白,吾家益貧,衣食不足以養,而大家之晚節更苦。嗚呼!其可痛也夫。
左擎蒼。右牽黃。昔日存心飛走忙。如今萬事忘。飲瓊漿。宴明堂。瑞氣祥光入絳房。無中得弄璋。
直望氤氳紫霧遙,萬重飛鞚馬蕭蕭。 鴛班虎隊皆戎服,兩度迎鑾德勝橋。
悚懼未成立,隱憂道學失。修身復補過,庶保馀生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