贈太平馬學博 其一
名山不在高,
名泉不在深。
所貴清冷色,
玩之怡我心。
之子山川秀,
沖懷寄遙岑。
六十困寒氈,
白首無知音。
丹室偶然遇,
蘭雪生我襟。
高話對微雨,
如聽松間琴。
契合各有數,
傾蓋比黃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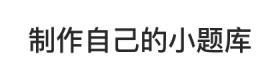
名山不在高,
名泉不在深。
所貴清冷色,
玩之怡我心。
之子山川秀,
沖懷寄遙岑。
六十困寒氈,
白首無知音。
丹室偶然遇,
蘭雪生我襟。
高話對微雨,
如聽松間琴。
契合各有數,
傾蓋比黃金。
有名的山不在于高度,有名的泉不在于深度。珍貴的是那清冽冷寂的色澤,觀賞它能讓我心情愉悅。您如山川般靈秀,淡泊的胸懷寄托于遠方的高山。六十歲仍困守清寒的學館,白發蒼蒼卻難遇知音。在書齋中偶然相遇,如蘭似雪的高潔氣質沁入我衣襟。與您在細雨中暢談高論,仿佛聆聽松間的琴聲。彼此投契自有緣分,初次相逢便勝過黃金般珍貴。
清冷色:清冽冷寂的色澤。
之子:這個人,此處指馬學博。
沖懷:淡泊的胸懷。
遙岑(cén):遠山。
寒氈:代指清寒的學館,學博為學官,此處形容其清苦境遇。
丹室:書齋。
蘭雪:比喻高潔的氣質,如蘭之雅、雪之潔。
傾蓋:原指兩車相遇時車蓋相傾,后喻指初交即投契的友人。
馬學博為學官,詩中提及“六十困寒氈”,可見其年事已高仍清苦守職。詩人或于書齋(丹室)與其偶然相遇,感其才德不遇、高潔難識,故作此詩贈之,以表欣賞與相知之情。
此詩通過自然意象與生活場景的結合,贊頌馬學博的高潔品格與淡泊胸懷,以“傾蓋比黃金”強調相遇投契的珍貴,語言質樸而情感真摯,體現了詩人對高潔人格的推崇與對真摯友情的珍視。
崇禎五年十二月,余住西湖。大雪三日,湖中人鳥聲俱絕。是日更定矣,余拏一小舟,擁毳衣爐火,獨往湖心亭看雪。霧凇沆碭,天與云與山與水,上下一白,湖上影子,惟長堤一痕、湖心亭一點、與余舟一芥、舟中人兩三粒而已。(余拏 一作:余挐)
到亭上,有兩人鋪氈對坐,一童子燒酒爐正沸。見余大喜曰:“湖中焉得更有此人!”拉余同飲。余強飲三大白而別。問其姓氏,是金陵人,客此。及下船,舟子喃喃曰:“莫說相公癡,更有癡似相公者。”
西湖七月半,一無可看,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。看七月半之人,以五類看之。其一,樓船簫鼓,峨冠盛筵,燈火優傒,聲光相亂,名為看月而實不見月者,看之。其一,亦船亦樓,名娃閨秀,攜及童孌,笑啼雜之,環坐露臺,左右盼望,身在月下而實不看月者,看之。其一,亦船亦聲歌,名妓閑僧,淺斟低唱,弱管輕絲,竹肉相發,亦在月下,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,看之。其一,不舟不車,不衫不幘,酒醉飯飽,呼群三五,躋入人叢,昭慶、斷橋,囂呼嘈雜,裝假醉,唱無腔曲,月亦看,看月者亦看,不看月者亦看,而實無一看者,看之。其一,小船輕幌,凈幾暖爐,茶鐺旋煮,素瓷靜遞,好友佳人,邀月同坐,或匿影樹下,或逃囂里湖,看月而人不見其看月之態,亦不作意看月者,看之。
杭人游湖,巳出酉歸,避月如仇。是夕好名,逐隊爭出,多犒門軍酒錢。轎夫擎燎,列俟岸上。一入舟,速舟子急放斷橋,趕入勝會。以故二鼓以前,人聲鼓吹,如沸如撼,如魘如囈,如聾如啞。大船小船一齊湊岸,一無所見,止見篙擊篙,舟觸舟,肩摩肩,面看面而已。少刻興盡,官府席散,皂隸喝道去。轎夫叫,船上人怖以關門,燈籠火把如列星,一一簇擁而去。岸上人亦逐隊趕門,漸稀漸薄,頃刻散盡矣。
吾輩始艤舟近岸,斷橋石磴始涼,席其上,呼客縱飲。此時月如鏡新磨,山復整妝,湖復靧面,向之淺斟低唱者出,匿影樹下者亦出。吾輩往通聲氣,拉與同坐。韻友來,名妓至,杯箸安,竹肉發。月色蒼涼,東方將白,客方散去。吾輩縱舟,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,香氣拍人,清夢甚愜。
陶庵國破家亡,無所歸止。披發入山,駴駴為野人。故舊見之,如毒藥猛獸,愕窒不敢與接。作《自挽詩》,每欲引決,因《石匱書》未成,尚視息人世。然瓶粟屢罄,不能舉火。始知首陽二老,直頭餓死,不食周粟,還是后人妝點語也。
饑餓之余,好弄筆墨。因思昔日生長王、謝,頗事豪華,今日罹此果報:以笠報顱,以蕢報踵,仇簪履也;以衲報裘,以苧報絺,仇輕煖也;以藿報肉,以糲報粻,仇甘旨也;以薦報床,以石報枕,仇溫柔也;以繩報樞,以甕報牖,仇爽塏也;以煙報目,以糞報鼻,仇香艷也;以途報足,以囊報肩,仇輿從也。種種罪案,從種種果報中見之。
雞鳴枕上,夜氣方回。因想余生平,繁華靡麗,過眼皆空,五十年來,總成一夢。今當黍熟黃粱,車旋蟻穴,當作如何消受?遙思往事,憶即書之,持向佛前,一一懺悔。不次歲月,異年譜也;不分門類,別《志林》也。偶拈一則,如游舊徑,如見故人,城郭人民,翻用自喜。真所謂“癡人前不得說夢”矣。
昔有西陵腳夫為人擔酒,失足破其甕。念無以償,癡坐佇想曰:“得是夢便好。”一寒士鄉試中式,方赴鹿鳴宴,恍然猶意未真,自嚙其臂曰:“莫是夢否?”一夢耳,惟恐其非夢,又惟恐其是夢,其為癡人則一也。
余今大夢將寤,猶事雕蟲,又是一番夢囈。因嘆慧業文人,名心難化,正如邯鄲夢斷,漏盡鐘鳴,盧生遺表,猶思摹拓二王,以流傳后世。則其名根一點,堅固如佛家舍利,劫火猛烈,猶燒之不失也。
蜀人張岱,陶庵其號也。少為紈绔子弟,極愛繁華,好精舍,好美婢,好孌童,好鮮衣,好美食,好駿馬,好華燈,好煙火,好梨園,好鼓吹,好古董,好花鳥,兼以茶淫橘虐,書蠹詩魔,勞碌半生,皆成夢幻。年至五十,國破家亡,避跡山居,所存者破床碎幾,折鼎病琴,與殘書數帙,缺硯一方而已。布衣蔬茛,常至斷炊。回首二十年前,真如隔世。
常自評之,有七不可解:向以韋布而上擬公侯,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,如此則貴賤紊矣,不可解一;產不及中人,而欲齊驅金谷,世頗多捷徑,而獨株守於陵,如此則貧富舛矣,不可解二;以書生而踐戎馬之場,以將軍而翻文章之府,如此則文武錯矣,不可解三;上陪玉帝而不諂,下陪悲田院乞兒而不驕,如此則尊卑溷矣,不可解四;弱則唾面而肯自干,強則單騎而能赴敵,如此則寬猛背矣,不可解五;爭利奪名,甘居人后,觀場游戲,肯讓人先,如此緩急謬矣,不可解六;博弈摴蒱,則不知勝負,啜茶嘗水,則能辨澠淄,如此則智愚雜矣,不可解七。有此七不可解,自且不解,安望人解?故稱之以富貴人可,稱之以貧賤人亦可;稱之以智慧人可,稱之以愚蠢人亦可;稱之以強項人可,稱之以柔弱人亦可;稱之以卞急人可,稱之以懶散人亦可。學書不成,學劍不成,學節義不成,學文章不成,學仙學佛,學農學圃俱不成,任世人呼之為敗家子,為廢物,為頑民,為鈍秀才,為瞌睡漢,為死老魅也已矣。
初字宗子,人稱石公,即字石公。好著書,其所成者,有《石匱書》《張氏家譜》《義烈傳》《瑯嬛文集》《明易》《大易用》《史闕》《四書遇》《夢憶》《說鈴》《昌谷解》《快園道古》《傒囊十集》《西湖夢尋》《一卷冰雪文》行世。生于萬歷丁酉八月二十五日卯時,魯國相大滌翁之樹子也,母曰陶宜人。幼多痰疾,養于外大母馬太夫人者十年。外太祖云谷公宦兩廣,藏生牛黃丸盈數簏,自余囡地以至十有六歲,食盡之而厥疾始廖。六歲時,大父雨若翁攜余之武林,遇眉公先生跨一角鹿,為錢塘游客,對大父曰:“聞文孫善屬對,吾面試之。”指屏上李白騎鯨圖曰:“太白騎鯨,采石江邊撈夜月。”余應曰:“眉公跨鹿,錢塘縣里打秋風。”眉公大笑起躍曰:“那得靈雋若此,吾小友也。”欲進余以千秋之業,豈料余之一事無成也哉?
甲申以后,悠悠忽忽,既不能覓死,又不能聊生,白發婆娑,猶視息人世。恐一旦溘先朝露,與草木同腐,因思古人如王無功、陶靖節、徐文長皆自作墓銘,余亦效顰為之。甫構思,覺人與文俱不佳,輟筆者再。雖然,第言吾之癖錯,則亦可傳也已。曾營生壙于項王里之雞頭山,友人李研齋題其壙曰:“嗚呼,有明著述鴻儒陶庵張長公之壙。”伯鸞高士,冢近要離,余故有取于項里也。明年,年躋七十,死與葬,其日月尚不知也,故不書。銘曰: 窮石崇,斗金谷。盲卞和,獻荊玉。老廉頗,戰涿鹿。贗龍門,開史局。饞東坡,餓孤竹。五羖大夫,焉能自鬻。空學陶潛,枉希梅福。必也尋三外野人,方曉我之衷曲。
于園在瓜洲步五里鋪,富人于五所園也。非顯者刺,則門鑰不得出。葆生叔同知瓜洲,攜余往,主人處處款之。
園中無他奇,奇在磊石。前堂石坡高二丈,上植果子松數棵,緣坡植牡丹、芍藥,人不得上,以實奇。后廳臨大池,池中奇峰絕壑,陡上陡下,人走池底,仰視蓮花反在天上,以空奇。臥房檻外,一壑旋下如螺螄纏,以幽陰深邃奇。再后一水閣,長如艇子,跨小河,四圍灌木蒙叢,禽鳥啾唧,如深山茂林,坐其中,頹然碧窈。瓜洲諸園亭,俱以假山顯,(胎于石,娠于磊石之手,男女于琢磨搜剔之主人),至于園可無憾矣。
故事,三江看潮,實無潮看。午后喧傳曰:“今年暗漲潮。”歲歲如之。
庚辰八月,吊朱恒岳少師至白洋,陳章侯、祁世培同席。海塘上呼看潮,余遄往,章侯、世培踵至。
立塘上,見潮頭一線,從海寧而來,直奔塘上。稍近,則隱隱露白,如驅千百群小鵝擘翼驚飛。漸近,噴沫濺花,蹴起如百萬雪獅,蔽江而下,怒雷鞭之,萬首鏃鏃,無敢后先。再近,則颶風逼之,勢欲拍岸而上。看者辟易,走避塘下。潮到塘,盡力一礴,水擊射,濺起數丈,著面皆濕。旋卷而右,龜山一擋,轟怒非常,炮碎龍湫,半空雪舞。看之驚眩,坐半日,顏始定。
先輩言:浙江潮頭,自龕、赭兩山漱激而起。白洋在兩山外,潮頭更大,何耶?
梁國楊氏子九歲,甚聰惠。孔君平詣其父,父不在,乃呼兒出。為設果,果有楊梅。孔指以示兒曰:“此是君家果。”兒應聲答曰:“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。”
荀巨伯遠看友人疾,值胡賊攻郡,友人語巨伯曰:“吾今死矣,子可去。”巨伯曰:“遠來相視,子令吾去,敗義以求生,豈荀巨伯所行邪?”賊既至,謂巨伯曰:“大軍至,一郡盡空,汝何男子,而敢獨止?“巨伯曰:“友人有疾,不忍委之,寧以我身代友人命。”賊相謂曰:“我輩無義之人,而入有義之國。”遂班軍而還,一郡并獲全。
有鸚鵡飛集他山,山中禽獸輒相貴重,鸚鵡自念:雖樂不可久也,便去。后數日,山中大火。鸚鵡遙見,便入水濡羽,飛而灑之。天神言:“汝雖有志,意何足云也。”對曰:“雖知不能,然吾嘗僑居是山,禽獸善行,皆為兄弟,不忍見耳。”天神嘉感,即為滅火。
詠雪
謝太傅寒雪日內集,與兒女講論文義。俄而雪驟,公欣然曰:“白雪紛紛何所似?”兄子胡兒曰:“撒鹽空中差可擬。”兄女曰:“未若柳絮因風起。”公大笑樂。即公大兄無奕女,左將軍王凝之妻也。
陳太丘與友期行
陳太丘與友期行,期日中。過中不至,太丘舍去,去后乃至。元方時年七歲,門外戲。客問元方:“尊君在不?”答曰:“待君久不至,已去。”友人便怒曰:“非人哉!與人期行,相委而去。”元方曰:“君與家君期日中。日中不至,則是無信;對子罵父,則是無禮。”友人慚,下車引之。元方入門不顧。
陳遺至孝。母喜食鐺底焦飯,遺作郡主簿,恒裝一囊,每煮食,輒貯收焦飯,歸而遺母。后值孫恩掠郡,郡守袁山松即日出征。時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,未及歸家,遂攜而從軍。與孫恩戰,敗,軍人潰散,遁入山澤,無以為糧,有饑餒而死者。遺獨以焦飯得活,時人以為至孝之報也。
周處年少時,兇強俠氣,為鄉里所患。又義興水中有蛟,山中有白額虎,并皆暴犯百姓。義興人謂為三橫,而處尤劇。
或說處殺虎斬蛟,實冀三橫唯余其一。處即刺殺虎,又入水擊蛟。蛟或浮或沒,行數十里,處與之俱。經三日三夜,鄉里皆謂已死,更相慶。
竟殺蛟而出,聞里人相慶,始知為人情所患,有自改意。
乃入吳尋二陸。平原不在,正見清河,具以情告,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,終無所成。清河曰:“古人貴朝聞夕死,況君前途尚可。且人患志之不立,何憂令名不彰邪?”處遂改勵,終為忠臣。
范文正公,蘇人也,平生好施與,擇其親而貧,疏而賢者,咸施之。
方貴顯時,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,號曰義田,以養濟群族之人。日有食,歲有衣,嫁娶兇葬,皆有贍。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,而時共出納焉。日食人一升,歲衣人一縑,嫁女者五十千,再嫁者三十千,娶婦者三十千,再娶者十五千,葬者如再嫁之數,葬幼者十千。族之聚者九十口,歲入給稻八百斛。以其所入,給其所聚,沛然有余而無窮。屏而家居俟代者與焉;仕而居官者罷其給。此其大較也。
初,公之未貴顯也,嘗有志于是矣,而力未逮者二十年。既而為西帥,及參大政,于是始有祿賜之入,而終其志。公既歿,后世子孫修其業,承其志,如公之存也。公雖位充祿厚,而貧終其身。歿之日,身無以為斂,子無以為喪,唯以施貧活族之義,遺其子而已。
昔晏平仲敝車羸馬,桓子曰:“是隱君之賜也。”晏子曰:“自臣之貴,父之族,無不乘車者;母之族,無不足于衣食者;妻之族,無凍餒者;齊國之士,待臣而舉火者,三百余人。以此而為隱君之賜乎?彰君之賜乎?”于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。予嘗愛晏子好仁,齊侯知賢,而桓子服義也。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,而言有次也;先父族,次母族,次妻族,而后及其疏遠之賢。孟子曰:“親親而仁民,仁民而愛物。”晏子為近之。觀文正之義,賢于平仲,其規模遠舉又疑過之。
嗚呼!世之都三公位,享萬鍾祿,其邸第之雄,車輿之飾,聲色之多,妻孥之富,止乎一己而已,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,豈少也哉!況于施賢乎!其下為卿,為大夫,為士,廩稍之充,奉養之厚,止乎一己而已;而族之人操瓢囊為溝中瘠者,又豈少哉?況于他人乎!是皆公之罪人也。
公之忠義滿朝廷,事業滿邊隅,功名滿天下,后必有史官書之者,予可無錄也。獨高其義,因以遺于世云。
文之難言也久矣,是使為文者紛綸,無人察其否臧焉;雷同相從,隨聲是非,遂令怨咨之音作,茍且之道開。荊璆無價,武夫有輝。仰惟執事,坐而相之,得不然乎?
當今朝廷洪雅尚文,以文化人,四方翕然,聽命于有司。有司于是乃以詞賦瑣能而軌度之,聲稱叢聞而搴擷之。謬矣哉!失在茲乎?原夫先作之立軌度者,懼常才之不及也,非罪其過也;抑亦有良材茂器,或所不識也,博聲稱者,有司之至公也,亦至私也。且聲稱之始,十九黨與,已乃惑之,識不自勝。襲私載公,是至私也。設有一人,乘語未終,而難觀曰:“軌度以考其能,違之者子何病?聲稱所以尋其實也,無之者子何病?”則曰:俞哉!非愿去軌度,塞聲稱,二者誠仕進之向也。蓋欲有司之留視于軌度之外者,綏聽于聲稱之遺者,勿以人之好惡,奪己之精理也。何者?慮良冶之巧,無消冰之術,鏌铘之銳,無補履之用,而因投棄,為代所笑耳。是說也,得不近之哉?實所未言于人,常用叩之執事耳。
觀長于江湖之鄉,學于仁義之書微有志義,仍近直方,不茍與人,亟于自求。從學兩年,屑屑焉人未之聞,名未之成,進取無嘉謨,環向多窮愁,視形如陋,視文如愚,憤之用勞,罔之攸安,欲如之何?執事文章之儲,文詞之師。扶微削訛,可以厚名;殫鑒垂哀,可以辨文。觀也于焉捧卷如歸,言莫卒微,不知悚兢。觀再拜。
春夜傷心坐畫屏,不如放眼入青冥。 一山突起丘陵妒,萬籟無言帝坐靈。 塞上似騰奇女氣,江東久殞少微星。 從來不蓄湘累問,喚出嫦娥詩與聽。(從來 一作:平生)
沉沉心事北南東,一睨人材海內空。 壯歲始參周史席,髫年惜墮晉賢風。 功高拜將成仙外,才盡回腸蕩氣中。 萬一禪關砉然破,美人如玉劍如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