賃宅
萍流匏系任行藏,惟指無何是我鄉。
左宦只拋紅藥案,僦居猶住玉泉坊。
白公渭北眠村舍,杜甫瀼西賃草堂。
未有吾廬莫惆悵,古來賢達盡茫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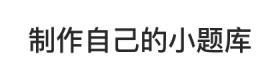
萍流匏系任行藏,惟指無何是我鄉。
左宦只拋紅藥案,僦居猶住玉泉坊。
白公渭北眠村舍,杜甫瀼西賃草堂。
未有吾廬莫惆悵,古來賢達盡茫茫。
如浮萍漂流、匏瓜系留般任隨命運的行止,只把沒有煩惱之地當作我的家鄉。降職外放只是拋下了那堆滿文書的辦公桌,租的居所還住在玉泉坊。白居易曾在渭北的村舍中居住,杜甫也曾在瀼西租了草堂。沒有自己的房子不要惆悵,自古以來賢達之人也都如此。
萍流匏系:比喻行蹤漂泊不定。行藏:指出處或行止。
無何:指無何有之鄉,即什么都沒有的地方,這里指沒有煩惱之地。
左宦:降職外放。紅藥案:指堆滿文書的辦公桌。
僦居:租屋居住。
白公:指白居易,他曾在渭北居住。杜甫曾在瀼西租草堂居住。
賢達:賢明通達的人。
具體創作時間不詳,推測詩人可能處于降職外放、居無定所的時期,看到自己的處境,聯想到古代賢達也有類似經歷,從而創作此詩自我寬慰。
這首詩主旨是表達詩人在漂泊無廬情況下的豁達,以古賢經歷自勉。特點是用典自然,情感豁達。在文學史上雖不著名,但體現了詩人面對困境的樂觀態度。
太宗威容儼肅,百僚進見者,皆失其舉措。太宗知其若此,每見人奏事,必假顏色,冀聞諫諍,知政教得失。貞觀初,嘗謂公卿曰:“人欲自照,必須明鏡;主欲知過,必藉忠臣。主若自賢,臣不匡正,欲不危敗,豈可得乎?故君失其國,臣亦不能獨全其家。至于隋煬帝暴虐,臣下鉗口,卒令不聞其過,遂至滅亡,虞世基等,尋亦誅死。前事不遠,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,必須極言規諫。”
貞觀元年,太宗謂侍臣曰:“正主任邪臣,不能致理;正臣事邪主,亦不能致理。惟君臣相遇,有同魚水,則海內可安。朕雖不明,幸諸公數相匡救,冀憑直言鯁議,致天下太平。”諫議大夫王珪對曰:“臣聞,木從繩則正,后從諫則圣。是故古者圣主必有爭臣七人,言而不用,則相繼以死。陛下開圣慮,納芻蕘,愚臣處不諱之朝,實愿罄其狂瞽。”太宗稱善,詔令自是宰相入內平章國計,必使諫官隨入,預聞政事。有所開說,必虛己納之。
貞觀五年,太宗謂房玄齡等曰:“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,喜則濫賞無功,怒則濫殺無罪。是以天下喪亂,莫不由此。朕今夙夜未嘗不以此為心,恒欲公等盡情極諫。公等亦須受人諫語,豈得以人言不同己意,便即護短不納?若不能受諫,安能諫人?”
貞觀八年,太宗謂侍臣曰:“朕每閑居靜坐,則自內省,恒恐上不稱天心,下為百姓所怨。但思正人匡諫,欲令耳目外通,下無怨滯。又比見人來奏事者,多有怖懾,言語致失次第。尋常奏事,情猶如此,況欲諫諍,必當畏犯逆鱗。所以每有諫者,縱不合朕心,朕亦不以為忤。若即嗔責,深恐人懷戰懼,豈肯更言!”
貞觀十六年,太宗謂房玄齡等曰:“自知者明,信為難矣。如屬文之士,伎巧之徒,皆自謂己長,他人不及。若名工文匠,商略詆訶,蕪詞拙跡,于是乃見。由是言之,人君須得匡諫之臣,舉其愆過。一日萬機,一人聽斷,雖復憂勞,安能盡善?常念魏徵隨事諫正,多中朕失,如明鏡鑒形,美惡必見。”因舉觴賜玄齡等數人勖之。
貞觀十七年,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:“昔舜造漆器,禹雕其俎,當時諫者十有余人。食器之間,何須苦諫?”遂良對曰:“雕琢害農事,纂組傷女工。首創奢淫,危亡之漸。漆器不已,必金為之;金器不已,必玉為之。所以諍臣必諫其漸,及其滿盈,無所復諫。”太宗曰:“卿言是矣。朕所為事,若有不當。或在其漸,或已將終,皆宜進諫。比見前史,或有人臣諫事,遂答云‘業已為之’,或道‘業已許之’,竟不為停改。此則危亡之禍,可反手而待也。”
貞觀初,太宗謂侍臣曰:“為君之道,必須先存百姓。若損百姓以奉其身,猶割股以啖腹,腹飽而身斃。若安天下,必須先正其身,未有身正而影曲,上治而下亂者。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,皆由嗜欲以成其禍。若耽嗜滋味,玩悅聲色,所欲既多,所損亦大,既妨政事,又擾生民。且復出一非理之言,萬姓為之解體,怨讟既作,離叛亦興。朕每思此,不敢縱逸。”諫議大夫魏征對曰:“古者圣哲之主,皆亦近取諸身,故能遠體諸物。昔楚聘詹何,問其治國之要,詹何對以修身之術。楚王又問治國何如,詹何曰:‘未聞身治而國亂者。’陛下所明,實同古義。”
貞觀初,太宗謂侍臣曰:“隋煬帝廣造宮室,以肆行幸。自西京至東都,離宮別館,相望道次,乃至并州、涿郡,無不悉然。馳道皆廣數百步,種樹以飾其傍。人力不堪,相聚為賊。逮至末年,尺土一人,非復己有。以此觀之,廣宮室,好行幸,竟有何益?此皆朕耳所聞,目所見,深以自誡。故不敢輕用人力,惟令百姓安靜,不有怨叛而已。”
貞觀十一年,太宗幸洛陽宮,泛舟于積翠池,顧謂侍臣曰:“此宮觀臺沼并煬帝所為,所謂驅役生民,窮此雕麗,復不能守此一都,以萬民為慮。好行幸不息,民所不堪。昔詩人云:‘何草不黃?何日不行?’‘小東大東,杼軸其空。’正謂此也。遂使天下怨叛,身死國滅,今其宮苑盡為我有。隋氏傾覆者,豈惟其君無道,亦由股肱無良。如宇文述、虞世基、裴蘊之徒,居高官,食厚祿,受人委任,惟行諂佞,蔽塞聰明,欲令其國無危,不可得也。”司空長孫無忌奏言:“隋氏之亡,其君則杜塞忠讜之言,臣則茍欲自全,左右有過,初不糾舉,寇盜滋蔓,亦不實陳。據此,即不惟天道,實由君臣不相匡弼。”太宗曰:“朕與卿等承其余弊,惟須弘道移風,使萬世永賴矣。”
貞觀十三年,太宗謂魏征等曰:“隋煬帝承文帝余業,海內殷阜,若能常處關中,豈有傾敗?遂不顧百姓,行幸無期,徑往江都,不納董純、崔象等諫諍,身戮國滅,為天下笑。雖復帝祚長短,委以玄天,而福善禍淫,亦由人事。朕每思之,若欲君臣長久,國無危敗,君有違失,臣須極言。朕聞卿等規諫,縱不能當時即從,再三思審,必擇善而用之。”
貞觀十二年,太宗東巡狩,將入洛,次于顯仁宮,宮苑官司多被責罰。侍中魏征進言曰:“陛下今幸洛州,為是舊征行處,庶其安定,故欲加恩故老。城郭之民未蒙德惠,官司苑監多及罪辜,或以供奉之物不精,又以不為獻食。此則不思止足,志在奢靡,既乖行幸本心,何以副百姓所望?隋主先命在下多作獻食,獻食不多,則有威罰。上之所好,下必有甚,競為無限,遂至滅亡。此非載籍所聞,陛下目所親見。為其無道,故天命陛下代之。當戰戰栗栗,每事省約,參蹤前列,昭訓子孫,奈何今日欲在人之下?陛下若以為足,今日不啻足矣;若以為不足,萬倍于此,亦不足也。”太宗大驚曰:“非公,朕不聞此言。自今已后,庶幾無如此事。”
久拋青簡束行幐,白鳥蒼蠅甚可憎。 身是蠹魚酬夙債,黃河浪里讀書燈。
范文正公仲淹貧悴,依睢陽朱氏家,常與一術者游。會術者病篤,使人呼文正而告曰:“吾善煉水銀為白金,吾兒幼,不足以付,今以付子。”即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志,內文正懷中,文正方辭避,而術者氣已絕。后十余年,文正為諫官,術者之子長,呼而告之曰:“而父有神術,昔之死也,以汝尚幼,故俾我收之。今汝成立,當以還汝。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,封志宛然。
睡起無聊倚舵樓,瞿塘西望路悠悠。 長江巨浪征人淚,一夜西風共白頭。
野田黃雀自為群,山叟相過話舊聞。 夜半飯牛呼婦起,明朝種樹是春分。
偶家長山下,遂與世途遠。 泉聲掛屋角,曉見池水滿。 日出生清華,風來送余善。 大化無端倪,寧謂心有眼。 床頭遺古書,歲月忽已晚。 玩之不能了,圣哲有憂患。
明招山中人,高義無等倫。 恨子弗見之,一去五百春。 我學如贅疣,未成先誤身。 誤身身不淑,誤世心不仁。
漢家天子鎮寰瀛,塞北羌胡未罷兵。 猛將謀臣徒自貴,蛾眉一笑塞塵清。
百年將半仕三已,五畝就荒天一涯。 豈有白衣來剝啄,一從烏帽自欹斜。 真成獨坐空搔首,門柳蕭蕭噪暮鴉。
秦筑長城比鐵牢,蕃戎不敢過臨洮。 雖然萬里連云際,爭及堯階三尺高。
漾舟雪浪映花顏,徐福攜將竟不還。 同作危時避秦客,此行何似武陵灘。
陸困泥蟠未適從,豈妨耕稼隱高蹤。 若非先主垂三顧,誰識茅廬一臥龍。
銅雀臺成玉座空,短歌長袖盡悲風。 不知仙駕歸何處,徒遣顰眉望漢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