桑貴有感
我老與時忤,十年守窮空。
衣食相驅迫,遂師田舍翁。
每當春蠶起,不敢怠微躬。
晨興督家人,留心曲箔中。
客寓無田園,專仰買桑供。
豈謂桑陡貴,半路哀涂窮。
三百變三千,十倍價何穹。
家貲已典盡,厥費猶未充。
乃知楮法壞,流毒刀兵同。
蒼天此何人,血面訴難通。
棄蠶滿阬谷,行當歌大東。
預憂兒女曹,凜洌當嚴風。
我窮何足道,四海關吾胸。
赤子已露立,視天猶夢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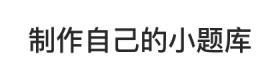
我老與時忤,十年守窮空。
衣食相驅迫,遂師田舍翁。
每當春蠶起,不敢怠微躬。
晨興督家人,留心曲箔中。
客寓無田園,專仰買桑供。
豈謂桑陡貴,半路哀涂窮。
三百變三千,十倍價何穹。
家貲已典盡,厥費猶未充。
乃知楮法壞,流毒刀兵同。
蒼天此何人,血面訴難通。
棄蠶滿阬谷,行當歌大東。
預憂兒女曹,凜洌當嚴風。
我窮何足道,四海關吾胸。
赤子已露立,視天猶夢夢。
我年老與時代不合,十年來一直守著貧窮。為衣食所迫,只能效仿農夫。每當春蠶孵化,不敢稍有懈怠。清晨督促家人,仔細查看蠶箔。客居他鄉沒有田園,只能靠買桑葉養蠶。沒想到桑葉價格暴漲,半路陷入困境。三百錢漲到三千,十倍的價格何等高昂。家中財物已典當一空,費用仍不夠。這才知道紙幣制度崩壞,流毒堪比刀兵。蒼天啊這是何人所為?血淚控訴難以傳達。棄蠶于山谷,即將唱起《大東》那樣的怨歌。擔憂兒女,如寒風凜冽。我窮算什么?四海都在我心中。百姓已無衣可穿,看天仍昏聵不明。
忤(wǔ):抵觸,不合。
師:效法,學習。
曲箔(bó):養蠶的竹簾,此處代指蠶房。
楮(chǔ)法:宋代紙幣制度,因紙幣用楮樹皮造紙制成,故稱。
大東:《詩經·小雅·大東》為東方諸侯國怨刺周王室的詩,此處代指百姓的苦難之音。
赤子:指平民百姓。
夢夢:昏聵不明的樣子。
詩作約創作于南宋后期紙幣(會子、交子)嚴重貶值時期。當時政府濫發紙幣導致物價飛漲,普通蠶農因依賴購買桑葉,首當其沖受桑價暴漲沖擊。作者作為客居無田的小生產者,親歷“桑陡貴”的經濟困境,進而反思貨幣制度崩壞對民生的摧殘,寫下此詩。
此詩以個人養蠶遭遇為切入點,真實反映南宋后期因紙幣制度崩潰引發的桑價暴漲、民生凋敝現象。通過具體生活場景的白描與對楮法的直接批判,展現了詩人“我窮何足道,四海關吾胸”的家國情懷,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與歷史史料價值。
春風如貴客,一到便繁華。 來掃千山雪,歸留萬國花。
歸雁低空,游蜂趁暖。憑高目向西云斷。具茨山外夕陽多,展江亭下春波滿。 雙桂情深,千花明煥。良辰誰是同游伴。辛夷花謝早梅開,應須次第調弦管。
夜來風橫雨飛狂,滿地閑花衰草。燕子漸歸春悄。簾幕垂清曉。 天將佳景與閑人,美酒寧嫌華皓。留取舊時歡笑。莫共秋光老。
青龍地脈土酥香。產玉似昆岡。可憐不入瑤池宴,到冰壺、風味凄涼。忽憶故園時序,春盤春酒羔羊。青絲生菜韭芽黃。銀縷染紅霜。桃花人面柔荑手,酒微酣、象箸頻將。鼙鼓一聲驚散,六年地老天荒。
神仙有無?安居華屋,即是蓬壺。榴花也學紅裙舞,燕雀喧呼。水晶盤饌供 麟脯,珊瑚鉤簾卷蝦須。吹龍笛,擊鼉鼓,年年初度,長日盡歡娛。 橫山翠屏,藏龍古井,走馬長汀。四時花竹多風景,勝似丹青。好兒郎天生 寧馨,好時節日見升平。氛埃靜,年年壽星,光照望云亭。
沉思十五年中事,才也縱橫,淚也縱橫,雙負簫心與劍名。 春來沒個關心夢,自懺飄零,不信飄零,請看床頭金字經。
好夢最難留,吹過仙洲。尋思依樣到心頭。去也無蹤尋也慣,一桁紅樓。 中有話綢繆,燈火簾鉤。是仙是幻是溫柔。獨自凄涼還自遣,自制離愁。
昆岡火烈去年時,玉也灰飛。石也灰飛。鶴長鳧短總休提。善有天知。惡有天知。今年快活保妻兒。歌也相宜。舞也相宜。揮金如土醉如泥。休負佳期。莫負佳期。
不是逢人苦譽君,亦狂亦俠亦溫文。 照人膽似秦時月,送我情如嶺上云。
松菜酒香春甕。更有麻姑相送。日日瀉流霞,添我胸中鉛汞。珍重。珍重。浮世本來如夢。
我又南行矣!笑今年、鸞飄鳳泊,情懷何似?縱使文章驚海內,紙上蒼生而已。似春水、干卿何事?暮雨忽來鴻雁杳,莽關山、一派秋聲里。催客去,去如水。 華年心緒從頭理,也何聊、看潮走馬,廣陵吳市。愿得黃金三百萬,交盡美人名士。更結盡、燕邯俠子。來歲長安春事早,勸杏花、斷莫相思死。木葉怨,罷論起。
飛雪初停酒未消,溪山深處踏瓊瑤。 不嫌寒氣侵入骨,貪看梅花過野橋。
天香浮玉露,金色艷高秋。 誰似雙棲者,相依共白頭。
性與雖天縱,主世乃無由。何言泰山毀,空驚逝水流。 及門思往烈,入室想前修。寂寞荒階暮,摧殘古木秋。 遺風曖如此,聊以慰蒸求。
初,范陽祖逖,少有大志,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。同寢,中夜聞雞鳴,蹴琨覺,曰:“此非惡聲也!”因起舞。及渡江,左丞相睿以為軍諮祭酒,逖居京口,糾合驍健,言于睿曰:“晉室之亂,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,由宗室爭權,自相魚肉,遂使戎狄乘隙,毒流中土。今遺民既遭殘賊,人思自奮,大王誠能命將出師,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,郡國豪杰必有望風響應者矣。”睿素無北伐之志,以逖為奮威將軍、州刺史,給千人廩,布三千匹,不給鎧仗,使自召募。秋八月,逖將其部曲百余家渡,中流,擊楫而誓曰:“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,有如大江!”遂屯淮陰,起冶鑄兵,募得二千余人而后進。逖既入譙城,石勒遣石虎圍譙,桓宣救之,虎解去。晉王傳檄天下,稱:“石虎敢帥犬羊,渡河縱毒,今遣九軍,銳卒三萬,水陸四道,徑造賊場,受祖逖節度。”大興三年,逖鎮雍丘,數遣兵邀擊后趙兵,后趙鎮戍歸逖者甚多,境漸蹙。秋七月,詔加逖鎮西將軍。逖在軍,與將士同甘苦,約己務施,勸課農桑,撫納附,雖疏賤者皆結以恩禮。逖練兵積谷,為取河北之計。后趙王勒患之,乃下幽州為逖修祖、父墓,置守冢二家,因與逖書,求通使及互市。逖不報書,而聽其互市,收利十倍。禁諸將不使侵暴后趙之民。邊境之間,稍得休息。四年秋七月,以尚書仆射戴淵為西將軍,鎮合肥,逖以已翦荊棘收河南地,而淵一旦來統之,意甚怏怏,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,將有內難。知大功不遂,感激發病。九月,卒于雍丘。豫州士女若喪父母,譙、梁間皆為立祠。祖逖既卒,后趙屢寇河南,拔襄城、城父,圍譙。豫州刺史祖約不能御,退屯壽春。后趙遂取陳留,梁、鄭之間復騷然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