送周架閣以浙東提干歸平江
共惟仁義心,無賢愚圣狂。
紛紛萬弓箭,獨以寸鐵當。
毫牦有不察,居然失其鄉。
察則我固有,而失豈真亡。
周君海內秀,清姿競球瑯。
牛刀十九年,猶顧善而藏。
用世無內外,意行獨安詳。
乃知旦晝物,特為弱者彊。
許時京塵中,解后兩匆忙。
前日同李郭,它日盟范張。
豈謂客逢客,乃或得相羊。
此道日寥落,此意誰平章。
為人作生活,悠悠老扶桑。
勉哉迪嘉猷,歲晚垂令芳。
我亦從此去,后會丘之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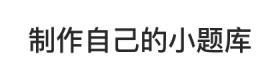
共惟仁義心,無賢愚圣狂。
紛紛萬弓箭,獨以寸鐵當。
毫牦有不察,居然失其鄉。
察則我固有,而失豈真亡。
周君海內秀,清姿競球瑯。
牛刀十九年,猶顧善而藏。
用世無內外,意行獨安詳。
乃知旦晝物,特為弱者彊。
許時京塵中,解后兩匆忙。
前日同李郭,它日盟范張。
豈謂客逢客,乃或得相羊。
此道日寥落,此意誰平章。
為人作生活,悠悠老扶桑。
勉哉迪嘉猷,歲晚垂令芳。
我亦從此去,后會丘之陽。
世人皆有仁義之心,無論賢愚圣狂皆具備。面對紛擾如萬箭齊發,唯以仁義寸鐵應對。若有絲毫未能明察,竟會迷失本真方向。明察則仁義本自固有,迷失又怎會真正消亡?周君乃海內才俊,姿容清俊如美玉琳瑯。十九年如牛刀小試,仍收斂才能待時藏。處世不論內外之境,心意從容自在安詳。可知白日里的紛擾,不過是弱者逞強之相。多時在京城塵土中,偶遇總是行色匆忙。前日曾與君同游,他日當結生死之盟。誰料客中逢客,竟得片刻悠閑徜徉。此道日益寥落,這份心意有誰評章?為人操勞生計,歲月悠悠漸老扶桑。望君勉力踐行善道,歲晚終能留下美名。我也將從此離去,后會當在山丘之陽。
架閣:宋代官名,掌管理檔案文書。
提干:提舉常平司干辦公事的簡稱,為地方監察官職。
球瑯:美玉,此處比喻周君品貌高潔。
牛刀:出自《論語·陽貨》“割雞焉用牛刀”,喻大材小用。
善而藏:化用《莊子·養生主》“善刀而藏之”,指收斂才能以待時。
李郭:東漢李膺、郭泰,二人相交為知己,此處喻指與周君的友情。
范張:范式、張劭,東漢人,以重諾守信著稱,喻生死之交。
相羊:同“徜徉”,悠閑自在。
平章:評議、辨別。
迪嘉猷(yóu):遵循善道,迪,遵循;猷,謀劃、道。
丘之陽:山丘的南邊,古代以山南為陽,此處指約定的再會地點。
此詩為送友人周架閣從浙東提干任上歸平江而作。周君久任地方(“牛刀十九年”),才德兼備卻低調內斂。詩人與周君在京城有過匆匆交集(“許時京塵中,解后兩匆忙”),此次客中相遇(“客逢客”)更添珍惜,故借送別之機,既贊其德才,又勉其踐行善道,反映南宋士人重道德、重友情的交游風氣。
全詩以“仁義心”為核心,先論道德本真,再贊友人德才,繼述相交情誼,終以勸勉作結,結構清晰。既體現儒家“仁義為本”的思想,又通過具體人物刻畫展現士人風骨,是一首情感真摯、理趣兼備的送別佳作。
巖巖梁山,積石峨峨。遠屬荊衡,近綴岷嶓。南通邛僰,北達褒斜。狹過彭碣,高逾嵩華。
惟蜀之門,作固作鎮。是曰劍閣,壁立千仞。窮地之險,極路之峻。世濁則逆,道清斯順。閉由往漢,開自有晉。
秦得百二,并吞諸侯。齊得十二,田生獻籌。矧茲狹隘,土之外區。一人荷戟,萬夫趑趄。形勝之地,匪親勿居。
昔在武侯,中流而喜。山河之固,見屈吳起。興實在德,險亦難恃。洞庭孟門,二國不祀。自古迄今,天命匪易。憑阻作昏,鮮不敗績。公孫既滅,劉氏銜璧。覆車之軌,無或重跡。勒銘山阿,敢告梁益。
田家樵采去,薄暮方來歸。 還聞稚子說,有客款柴扉。 儐從皆珠玳,裘馬悉輕肥。 軒蓋照墟落,傳瑞生光輝。 疑是徐方牧,既是復疑非。 思舊昔言有,此道今已微。 物情棄疵賤,何獨顧衡闈? 恨不具雞黍,得與故人揮。 懷情徒草草,淚下空霏霏。 寄書云間雁,為我西北飛。
風雨替花愁。風雨罷,花也應休。勸君莫惜花前醉,今年花謝,明年花謝,白了人頭。 乘興兩三甌。揀溪山好處追游。但教有酒身無事,有花也好,無花也好,選甚春秋。
昔擬栩仙人王云鶴贈予詩云:“寄與閑閑傲浪仙,枉隨詩酒墮凡緣。黃塵遮斷來時路,不到蓬山五百年。”其后玉龜山人云:“子前身赤城子也。”予因以詩寄之云:“玉龜山下古仙真,許我天臺一化身。擬折玉蓮聞白鶴,他年滄海看揚塵。”吾友趙禮部庭玉說,丹陽子謂予再世蘇子美也。赤城子則吾豈敢,若子美則庶幾焉。尚愧辭翰微不及耳。因作此以寄意焉。
四明有狂客,呼我謫仙人。俗緣千劫不盡,回首落紅塵。我欲騎鯨歸去,只恐神仙官府,嫌我醉時真。笑拍群仙手,幾度夢中身。 倚長松,聊拂石,坐看云。忽然黑霓落手,醉舞紫毫春。寄語滄浪流水,曾識閑閑居士,好為濯冠巾。卻返天臺去,華發散麒麟。
慶歷四年春,滕子京謫守巴陵郡。越明年,政通人和,百廢具興,乃重修岳陽樓,增其舊制,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,屬予作文以記之。(具 通:俱)
予觀夫巴陵勝狀,在洞庭一湖。銜遠山,吞長江,浩浩湯湯,橫無際涯,朝暉夕陰,氣象萬千,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,前人之述備矣。然則北通巫峽,南極瀟湘,遷客騷人,多會于此,覽物之情,得無異乎?
若夫淫雨霏霏,連月不開,陰風怒號,濁浪排空,日星隱曜,山岳潛形,商旅不行,檣傾楫摧,薄暮冥冥,虎嘯猿啼。登斯樓也,則有去國懷鄉,憂讒畏譏,滿目蕭然,感極而悲者矣。(隱曜 一作:隱耀;淫雨 通:霪雨)
至若春和景明,波瀾不驚,上下天光,一碧萬頃,沙鷗翔集,錦鱗游泳,岸芷汀蘭,郁郁青青。而或長煙一空,皓月千里,浮光躍金,靜影沉璧,漁歌互答,此樂何極!登斯樓也,則有心曠神怡,寵辱偕忘,把酒臨風,其喜洋洋者矣。
嗟夫!予嘗求古仁人之心,或異二者之為,何哉?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,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,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。是進亦憂,退亦憂。然則何時而樂耶?其必曰:“先天下之憂而憂,后天下之樂而樂”乎!噫!微斯人,吾誰與歸?
時六年九月十五日。
先生,漢光武之故人也。相尚以道。及帝握《赤符》,乘六龍,得圣人之時,臣妾億兆,天下孰加焉?惟先生以節高之。既而動星象,歸江湖,得圣人之清。泥涂軒冕,天下孰加焉?惟光武以禮下之。
在《蠱》之上九,眾方有為,而獨“不事王侯,高尚其事”,先生以之。在《屯》之初九,陽德方亨,而能“以貴下賤,大得民也”,光武以之。蓋先生之心,出乎日月之上;光武之量,包乎天地之外。微先生,不能成光武之大,微光武,豈能遂先生之高哉?而使貪夫廉,懦夫立,是大有功于名教也。
仲淹來守是邦,始構堂而奠焉,乃復為其后者四家,以奉祠事。又從而歌曰∶“云山蒼蒼,江水泱泱,先生之風,山高水長!”
騏驥筋力成,意在萬里外。厯塊一蹶,斃於空谷。唯馀駿骨,價重千金。大鵬羽翼張,勢欲摩穹昊。天風不來,海波不起。塌翅別島,空留大名。人亦有之,故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之謂矣。
公名白,字太白,其先隴西成紀人。絕嗣之家,難求譜諜。公之孫女搜於箱篋中,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數行,紙壞字缺,不能詳備。約而計之,涼武昭王九代孫也。隋末多難,一房被竄於碎葉,流離散落,隱易姓名。故自國朝已來,漏於屬籍。神龍初,潛還廣漢。因僑為郡人。父客,以逋其邑,遂以客為名。高臥云林,不求祿仕。公之生也,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,先夫人夢長庚而告祥,名之與字,咸所取象。受五行之剛氣,叔夜心高;挺三蜀之雄才,相如文逸。瑰奇宏廓,拔俗無類。少以俠自任,而門多長者車。常欲一鳴驚人,一飛沖天,彼漸陸遷喬,皆不能也。由是慷慨自負,不拘常調,器度宏大,聲聞於天。
天寶初,召見於金鑾殿,元宗明皇帝降輦步迎,如見園、綺,論當世務,草答蕃書,辯如懸河,筆不停綴。元宗嘉之,以寶床方丈賜食於前,御手和羹,德音褒美。褐衣恩遇,前無比儔。遂直翰林,專掌密命。將處司言之任,多陪侍從之游。他日,泛白蓮池,公不在宴。皇歡既洽,召公作序。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,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,優寵如是。布衣之遇,前所未聞。公自量疏遠之懷,難久於密侍,候間上疏,請還舊山。元宗甚愛其才,或慮乘醉出入省中,不能不言溫室樹,恐掇後患,惜而遂之。
公以為千鈞之弩,一發不中,則當摧撞折牙,而永息機用,安能效碌碌者蘇而復上哉!脫屣軒冕,釋羈韁鏁,因肆情性,大放於宇宙間。飲酒非嗜其酣樂,取其昏以自豪;作詩非事於文律,取其吟以自適。好神仙非慕其輕舉,將以不可求之事求之。其意欲耗壯心,遣馀年也。在長安時,秘書監賀知章號公為謫仙人。吟公《烏棲曲》云:“此詩可以哭鬼神矣。”時人又以公及賀監、汝陽王、崔宗之、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。朝列賦謫仙歌百馀首。俄屬戎馬生郊,遠身海上,往來於斗牛之分,優游沒身。偶乘扁舟,一日千里;或遇勝境,終年不移。時長江遠山,一泉一石,無往而不自得也。晚歲度牛渚磯,至姑熟,悅謝家青山,有終焉之志。盤桓庀居,竟卒於此。其生也,圣朝之高士;其死也,當涂之旅人。
代宗之初,搜羅俊逸,拜公左拾遺。制下於彤庭,禮降於元壤。生不及祿,歿而稱官,嗚呼命歟!
傳正共生唐代,甲子相懸,常於先大夫文字中,見與公有潯陽夜宴詩,則知與公有通家之舊。早於人間得公遺篇逸句,吟詠在口。無何,叨蒙恩獎,廉問宣、池。桉圖得公之墳墓,在當涂邑。因令禁樵采,備灑掃,訪公之子孫,將申慰薦。凡三四年,乃獲後女二人,一為陳云之室,一乃劉勸之妻,皆編戶甿也。因召至郡庭,相見與語,衣服村落,形容樸野,而進退閑雅,應對詳諦,且祖德如在,儒風宛然。問其所以,則曰:“父伯禽,以貞元八年不祿而卒,有兄一人,出游一十二年,不知所在。父存無官,父歿為民,有兄不相保,為天下之窮人。無桑以自蠶,非不知機杼;無田以自力,非不知稼穡。況婦人不任,布裙糲食,何所仰給?儷於農夫,救死而已。久不敢聞於縣官,懼辱祖考。鄉閭逼迫,忍恥來告。”言訖淚下,余亦對之泫然。因云:“先祖志在青山,遺言宅兆,頃屬多故,殯於龍山東麓,地近而非本意。墳高三尺,日益摧圯,力所不及,知如之何。”聞之憫然,將遂其請。因當涂令諸葛縱會計在州,得諭其事。縱亦好事者,學為歌詩,樂聞其語。便道還縣,躬相地形,卜新宅於青山之陽,以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,遷神於此。遂公之志也。西去舊墳六里,南抵驛路三百步。北倚謝公山,即青山也。天寶十二載敕改名焉。因告二女,將改適於士族。皆曰:“夫妻之道命也,亦分也。在孤窮既失身於下俚,仗威力乃求援於他門。生縱偷安,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下?欲敗其類,所不忍聞。”余亦嘉之,不奪其志,復井稅免徭役而已。今士大夫之葬,必志於墓,有勛庸道德之家,兼樹碑於道。余才術貧虛,不能兩致。今作新墓銘,輒刊二石,一寘於泉扃,一表於道路。亦峴首漢川之義也。庶芳聲之不泯焉。文集二十卷,或得之於時之文士,或得之於公之宗族,編緝斷簡,以行於代。銘曰:
“嵩岳降神,是生輔臣。蓬萊譴真,斯為逸人。晉有七賢,唐稱八仙。應彼星象,唯公一焉。晦以麴糵,暢於文篇。萬象奔走乎筆端,萬慮泯滅乎樽前。臥必酒甕,行惟酒船。吟風詠月,席地幕天。但貴乎適其所適,不知夫所以然而然。至今尚疑其醉在千日,寧審乎壽終百年。謝家山兮公之墓。異代詩流同此路。舊墳卑庳風雨侵。新宅爽塏松柏林。故鄉萬里且無嗣,二女從民永於此。猗歟琢石為二碑,一藏幽隧一臨歧。岸深谷高變化時,一存一毀名不虧。”
何處鐘聲。誰家笛韻,最是多情。獨步芳階,芭蕉月上,影落疏欞。
連朝腐草無螢。窗兒外、風清月明。寶篆拋煙,銀燈無焰,倍覺凄清。
予弱冠之年,隨牒江東漕闈,嘗與友人暇日命酒層樓。不惟鐘阜、石城之勝,班班在目,而平淮如席,亦橫陳樽俎間。既而北歷淮山,自齊安溯江泛湖,薄游巴陵,又得登岳陽樓,以盡荊州之偉觀。孫劉虎視遺跡依然,山川草木,差強人意。洎回京師,日詣豐樂樓以觀西湖。因誦友人“東南嫵媚,雌了男兒”之句,嘆息者久之。酒酣,大書東壁,以寫胸中之勃郁。時嘉熙庚子秋季下浣也。
記上層樓,與岳陽樓,釃酒賦詩。望長山遠水,荊州形勝,夕陽枯木,六代興衰。扶起仲謀,喚回玄德,笑殺景升豚犬兒。歸來也,對西湖嘆息,是夢耶非? 諸君傅粉涂脂,問南北戰爭都不知。恨孤山霜重,梅凋老葉;平堤雨急,柳泣殘絲。玉壘騰煙,珠淮飛浪,萬里腥風送鼓鼙。原夫輩,算事今如此,安用毛錐?
金樽清酒斗十千,玉盤珍羞直萬錢。(羞 同:饈;直 同:值) 停杯投箸不能食,拔劍四顧心茫然。 欲渡黃河冰塞川,將登太行雪滿山。(雪滿山 一作:雪暗天) 閑來垂釣碧溪上,忽復乘舟夢日邊。(碧 一作:坐) 行路難,行路難,多歧路,今安在? 長風破浪會有時,直掛云帆濟滄海。
一帶青松,半灣綠水,此是誰家位置。拊膺惆悵,低首沈吟,說甚平泉興替。
想為燕去梁空,總到春來。一年長閉。剩虬梅幾樹,有時和雨,暗垂香淚。
問昔日金谷亭臺,藥欄花嶼,只有青山曾記。痛深繡虎,腸斷西州,我比羊曇憔悴。
門對晴巒,杜鵑還似當年,怨紅啼翠。記未園詩句,吟向暮鐘聲里。
春風真解事,等閑吹遍,無數短長亭。 一星星是恨,直送春歸,替了落花聲。 憑闌極目,蕩春波、萬種春情。 應笑人舂糧幾許? 便要數征程。 冥冥,車輪落日,散綺余霞,漸都迷幻景。 問收向紅窗畫篋,可算飄零? 相逢只有浮云好,奈蓬萊東指,弱水盈盈。 休更惜,秋風吹老莼羹。
丹溪翁者,婺之義烏人也,姓朱氏,諱震亨,字彥修,學者尊之曰丹溪翁。翁自幼好學,日記千言。稍長,從鄉先生治經,為舉子業。后聞許文懿公得朱子四傳之學,講道八華山,復往拜焉。益聞道德性命之說,宏深粹密,遂為專門。一日,文懿謂曰:“吾臥病久,非精于醫者,不能以起之。子聰明異常人,其肯游藝于醫乎?”翁以母病脾,于醫亦粗習,及聞文懿之言,即慨然曰:“士茍精一藝,以推及物之仁,雖不仕于時,猶仕也。”乃悉焚棄向所習舉子業,一于醫致力焉。
時方盛行陳師文、裴宗元所定《大觀二百九十七方》,翁窮晝夜是習。既而悟曰:“操古方以治今病,其勢不能以盡合。茍將起度量,立規矩,稱權衡,必也《素》、《難》諸經乎!然吾鄉諸醫鮮克知之者。”遂治裝出游,求他師而叩之。乃渡浙河,走吳中,出宛陵,抵南徐,達建業,皆無所遇。及還武林,忽有以其郡羅氏告者。羅名知悌,字子敬,世稱太無先生,宋理宗朝寺人,學精于醫,得金劉完素之再傳,而旁通張從正、李杲二家之說。然性褊甚,恃能厭事,難得意。翁往謁焉,凡數往返,不與接。已而求見愈篤,羅乃進之,曰:“子非朱彥修乎?”時翁已有醫名,羅故知之。翁既得見,遂北面再拜以謁,受其所教。羅遇翁亦甚歡,即授以劉、李、張諸書,為之敷揚三家之旨,而一斷于經,且曰:“盡去而舊學,非是也。”翁聞其言,渙焉無少凝滯于胸臆。居無何,盡得其學以歸。
鄉之諸醫泥陳、裴之學者,聞翁言,即大驚而笑且排,獨文懿喜曰:“吾疾其遂瘳矣乎!”文懿得末疾,醫不能療者十余年,翁以其法治之,良驗,于是諸醫之笑且排者,始皆心服口譽。數年之間,聲聞頓著。翁不自滿足,益以三家之說推廣之。謂劉、張之學,其論臟腑氣化有六,而于濕熱相火三氣致病為最多,遂以推陳致新瀉火之法療之,此固高出前代矣。然有陰虛火動,或陰陽兩虛濕熱自盛者,又當消息而用之。謂李之論飲食勞倦,內傷脾胃,則胃脘之陽不能以升舉,并及心肺之氣,陷入中焦,而用補中益氣之劑治之,此亦前人之所無也。然天不足于西北,地不滿于東南。天,陽也;地,陰也。西北之人,陽氣易于降;東南之人,陰火易于升。茍不知此,而徒守其法,則氣之降者固可愈,而于其升者亦從而用之,吾恐反增其病矣。乃以三家之論,去其短而用其長,又復參之以太極之理,《易》、《禮記》、《通書》、《正蒙》諸書之義,貫穿《內經》之言,以尋其指歸。而謂《內經》之言火,蓋與太極動而生陽、五性感動之說有合;其言陰道虛,則又與《禮記》之養陰意同。因作《相火》及《陽有余陰不足》二論,以發揮之。
于是,翁之醫益聞。四方以病來迎者,遂輻湊于道,翁咸往赴之。其所治病凡幾,病之狀何如,施何良方,飲何藥而愈,自前至今,驗者何人,何縣里,主名,得諸見聞,班班可紀。
浦江鄭義士病滯下,一夕忽昏仆,目上視,溲注而汗泄。翁診之,脈大無倫,即告曰:“此陰虛而陽暴絕也,蓋得之病后酒且內,然吾能愈之。”即命治人參膏,而且促灸其氣海。頃之手動,又頃而脣動。及參膏成,三飲之蘇矣。其后服參膏盡數斤,病已。
天臺周進士病惡寒,雖暑亦必以綿蒙其首,服附子數百,增劇。翁診之,脈滑而數,即告曰:“此熱甚而反寒也。”乃以辛涼之劑,吐痰一升許,而蒙首之綿減半;仍用防風通圣飲之,愈。周固喜甚,翁曰:“病愈后須淡食以養胃,內觀以養神,則水可生,火可降;否則,附毒必發,殆不可救。”彼不能然,后告疽發背死。
一男子病小便不通,醫治以利藥,益甚。翁診之,右寸頗弦滑,曰:“此積痰病也,積痰在肺。肺為上焦,而膀胱為下焦,上焦閉則下焦塞,辟如滴水之器,必上竅通而后下竅之水出焉。”乃以法大吐之,吐已,病如失。
一婦人產后有物不上如衣裾,醫不能喻。翁曰:“此子宮也,氣血虛,故隨子而下。”即與黃芪當歸之劑,而加升麻舉之,仍用皮工之法,以五倍子作湯洗濯,皺其皮。少選,子宮上,翁慰之曰:“三年后可再生兒,無憂也。”如之。
一貧婦寡居病癩,翁見之惻然,乃曰:“是疾世號難治者,不守禁忌耳。是婦貧而無厚味,寡而無欲,庶幾可療也。”即自具藥療之,病愈。后復投四物湯數百,遂不發動。
翁之為醫,皆此類也。蓋其遇病施治,不膠于古方,而所療則中;然于諸家方論,則靡所不通。他人靳靳守古,翁則操縱取舍,而卒與古合。一時學者咸聲隨影附,翁敎之亹亹忘疲。
翁春秋既高,乃徇張翼等所請,而著《格致余論》、《局方發揮》、《傷寒辨疑》、《本草衍義補遺》、《外科精要新論》諸書,學者多誦習而取則焉。
翁簡愨貞良,剛嚴介特,執心以正,立身以誠,而孝友之行,實本乎天質。奉時祀也,訂其禮文而敬泣之。事母夫人也,時其節宣以忠養之。寧歉于己,而必致豐于兄弟;寧薄于己子,而必施厚于兄弟之子。非其友不友,非其道不道。好論古今得失,慨然有天下之憂。世之名公卿多折節下之,翁為直陳治道,無所顧忌。然但語及榮利事,則拂衣而起。與人交,一以三綱五紀為去就。嘗曰:天下有道,則行有枝葉;天下無道,則辭有枝葉。夫行,本也;辭,從而生者也。茍見枝葉之辭,去本而末是務,輒怒溢顏面,若將浼焉。翁之卓卓如是,則醫特一事而已。然翁講學行事之大方,已具吾友宋太史濂所為翁墓志,茲故不錄,而竊錄其醫之可傳者為翁傳,庶使后之君子得以互考焉。
論曰:昔漢嚴君平,博學無不通,賣卜成都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,則依蓍龜為陳其利害。與人子言,依于孝;與人弟言,依于順;與人臣言,依于忠。史稱其風聲氣節,足以激貪而厲俗。翁在婺得道學之源委,而混跡于醫。或以醫來見者,未嘗不以葆精毓神開其心。至于一語一默,一出一處,凡有關于倫理者,尤諄諄訓誨,使人奮迅感慨激厲之不暇。左丘明有云:“仁人之言,其利溥哉!”信矣。若翁者,殆古所謂直諒多聞之益友,又可以醫師少之哉?
滿眼生機轉化鈞,天工人巧日爭新。 預支五百年新意,到了千年又覺陳。
李杜詩篇萬口傳,至今已覺不新鮮。 江山代有才人出,各領風騷數百年。
只眼須憑自主張,紛紛藝苑漫雌黃。 矮人看戲何曾見,都是隨人說短長。
少時學語苦難圓,只道工夫半未全。 到老始知非力取,三分人事七分天。
詩解窮人我未空,想因詩尚不曾工。 熊魚自笑貪心甚,既要工詩又怕窮。
巖前流水碧潺潺,鶴馭翩翩去復還。堪笑世人求不死,豈知得道有無閒。